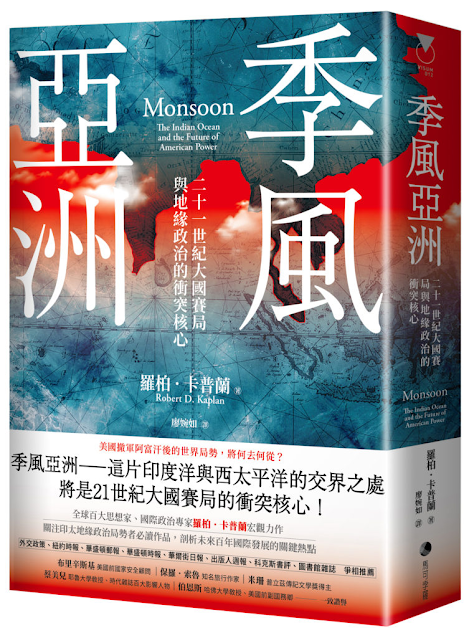马可孛罗出版 2021 年 12 月 9 日
第十五章 中国的两洋战略
五百多年前,印度洋已经为西方的征服大戏搭好舞台。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把由亨利王子和航海家达伽马所开启,葡萄牙掌控欧亚非海上航线的局面看成「现代的来临」。继葡萄牙之后,我们看到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和美国等国,在印度洋及其邻近海域重要地区留下印记。这些西方征服者多半是基于商业理由而来,特别是美国决心保卫海路交通,以便安全无虞地从印度洋西半部运送中东原油,不过他们也保卫着狄亚哥加西亚环礁的中央区域,而且利用这个英国领土做为基地,分别在一九九九年对伊拉克、二○○一年对阿富汗发动空袭。
冷战年代见证了美国成为全球海上强权,苏联则是宰制欧亚的陆上大国。随着冷战走入历史,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崛起,实际上,当美国攻打伊拉克和阿富汗陷入泥淖之际,一个新兴又更繁复的秩序正在欧亚大陆海洋边缘地带逐渐壮大,这个海洋边缘地带不仅涵盖印度洋,也包括了西太平洋。相伴而来的分析指出,美国海军的主导地位已经达到顶点,面对中国在海上扩张势力,加上印度的崛起,预示着西方在这些海域的掌控即将告终。
回顾过去,二○○四年十二月至二○○五年一月,美国军方为了援助南亚海啸的遇难者,在苏门答腊外海展开救灾行动,我们也许可以将这项行动看成美国在亚洲的海上军力达到巅峰。航母打击群和远征打击群出现在海面上,伴随着巡洋舰、驱逐舰及护航舰;直升机自舱面腾空升起,在船舰和海岸之间巡回飞行,以及救生员和海军医护官进一步支援的景象,产生一种威武和美德兼具、令人激动的氛围──这两种特质很难得并存。尽管「统一援助行动」(Operation Unified Assistance)是出于人道精神,但它使用的技术堪称是作战等级,几乎是一接获消息,就立刻集结大批战舰和飞机,以「最快速度」横渡数百英里海域。这次救援行动所释放的真正讯息是,「看看美国海军实力多么强大!」
在这军威浩大表面下的真实情况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美国简直把印度洋和西太平洋当成军事湖泊超过六十年后,它在这片海域正逐渐失去主导地位。美国民营智库机构「战略预测中心」(Strategic Forecasting)的国安分析指出,这样发展下去,再过几年,假使南亚和东南亚海域上又发生灾难,美国将不再是主要救灾者,无法提供同样强度的援助。在下一次的紧急救援行动中,美国军舰将与来自澳洲、日本、南韩、印度,可能还有中国的新「大舰」(big decks)分享这片海域(及荣耀)。与此同时,中国生产和取得的潜舰是美国的数倍之多,它确实兴起了造船热和购舰热,因此在未来十年间,人民解放军拥有的船舰将比美国海军还多。当然我们将会看到,数字只是全貌的一小部分,不过还是很重要。
不可否认,美国海军过去数十年来一直缩减。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拥有六千七百艘军舰;在冷战时期有六百艘左右;目前则少于两百八十艘。虽然海军计画把军舰增加到三百一十艘以上,但其他因素姑且不谈,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和国会研究处,这项成本已超支百分之三十四,意味着这个计画过分乐观。接下来的十年或更久,假使海军持续每年仅建造七艘军舰,而一支舰队的寿命是三十年,那么可以想见,军舰总数将缩减到两百艘以下。考量到美国的经济衰退,五角大厦的预算很可能进一步被削减,而「军舰开发」这非常昂贵的资本项目将首当其冲。
不过这并不代表美国海军很快会让出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优势地位。以上引用数字指出一种缓慢趋势,但情势也可能出现逆转。不过这确实意味着,二战结束后将近七十年,除了美国海军外,出没于那片海域的一概是本地区域国家的海军,以及海盗之类的非国家行为体(non-state actors),这些势力终究会慢慢挤进这个海上局面。美国在全球海域独大的「单极时代」正慢慢过去。就像前面所提到的,而在这个过程里,中国(极可能在二十一世纪与美国平起平坐的竞争者)正逐渐把经济影响力转成海上力量。
值得再次重申的是,中国军力的崛起没有不合法之处。中国取得优势地位的过程可以跟美国过去的情况两相对照。从南北内战和大西部开拓之后,美国巩固了陆地大国的地位,国势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开凿巴拿马运河时达到高点。在容易被人遗忘的几位总统(海斯、加菲尔德、阿瑟、哈里逊等)执政期间,美国经济随着高年均增长率悄然前进。因此,当美国与外在世界的贸易活动增加,首度在遥远地区发展出经济和战略的复合利益,随即促使美国海军与海军陆战队在南美和太平洋登陆,当然还有其他的军事行动。因此,我们何以期待中国会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中国社会的生机勃勃,跟一百年前的美国社会并无二致。
一八九○年,美国军事理论家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出版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六六○至一七八三》(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书中指出一个国家捍卫其商船舰队的武力,在世界历史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马汉的思想一直受主张制海权的人士推崇,当今中国和印度的战略家也都热切钻研他的著作。若说中国取得海权只是为了成为区域霸权或全球霸权的手段,这说法太过轻率。帝国的态势通常不是有意追求而来。相反地,一个国家愈来愈强大,就会发展出需求,以及有违直觉地生出一种新的不安全感,致使它积极往海外扩张。
中国不是艾哈迈迪内贾德总统所统治的伊朗,它没有威吓要摧毁任何国家,而且密切与美国在外交和经济方面发展关系。全球经济萧条甚至把美国和中国的利益绑得更紧,因为美国依赖中国提供的低廉产品,也靠中国数兆美元的外汇存底支撑美元,而中国则依赖美国做为它主要的消费市场。强劲的美中双边关系向前进展不仅煞有其事,而且对二十一世纪全球体系而言也许是最好的情况,真正的全球治理(world governance)得以因此而成形。
就形式上来说,中国并不民主,但它的体制容许针对政策和社会发展方向进行激烈、活跃的辩论。中国甚至可能面临某种内部动乱,导致领导阶层分裂,使它晋身大国地位的进程拖延数年甚至更久。一九七○年代,苏联政体研究者对苏联情势误判,错估冷战会再持续数十年;同样地,我跟其他人一开始就假定中国经济会持续成长,也很可能是误判。不过以目前的态势来说,仍必须严肃看待这样持续成长的可能性。
因此我认为,美中之间最可能出现一种非常微妙,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未来的美中对抗,尤其是在经济和外交事务上,将为「巧妙」一词赋予新义。但假如这关系出现剑拔弩张的局面,我预料其中之一会是两国海军的交锋,地点在大印度洋地区和西太平洋。
美国船舰的采购程序一直被形容为意兴阑珊,尽管国内生产毛额成长率减少──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美国仍努力维持海军现有的规模。而中国即使受到全球危机波及,过去二十年的国防预算却以两位数的速度持续增加,而未来几年中国经济成长率粗估将以每年百分之八至十增长。中国的水下军备包括十二艘配备尾流自导鱼雷的基洛级(kilo-class)柴油动力导弹攻击潜舰、十三艘宋级(Song-class)潜舰、两艘商级(Shang-class)核潜舰,以及一艘晋级(Jin-class)弹道飞弹核动力潜舰,还有三艘即将到位。
显然,这种阵容无论如何都比不上美国海军现役的七十四艘核动力攻击潜舰及导弹潜舰。美国自豪于拥有全世界三十四艘航母中的二十四艘,而中国则一艘也没有(不过有一艘或两艘正在研发中)。这类统计数字不胜枚举,但再次重申,数字不能代表全貌,实际情况关乎潜在趋势、不对称战事的能耐,以及海军、经济与区域权力的创造性组合,这能够在亚洲各地开拓势力范围。
中国正慢慢迎头赶上,但速度已快到足以发出警示,美国在海上称霸不会长长久久。当伊拉克用路边炸弹向美国显示粗糙、低阶科技的非对称战力,中国挟着发展导弹和太空计画,透过劝戒和反介入(access-denia)计谋,向美国展示细腻高阶科技的非对称战力:将来美国海军航母战斗群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要更靠近亚洲大陆,都得冒着更大的风险。中国位居亚洲地理中心,加上其不断增长的海军军力和新兴蓬勃的经济力量,将使美国持续在亚洲失去影响力。
有鉴于此,概述中国在印度洋和太平洋逐步成形的海军战略至关紧要。但在此之前,我有必要再多著墨中国为何转向海洋。具体来说,它正在发展的经济及战略复合利益中,哪些能跟一个世纪前美国的自身利益略微相比?
中国自古以来总忙于防范国土遭外族入侵。西元前三世纪开始修筑的长城,目的是抵挡匈奴人入侵;中苏在二十世纪中期交恶后,中国忧心北方的苏联发动另一次入侵,因此在毛泽东主政时期,国防预算集中于陆军,刻意忽略海洋。但随着苏联解体,这种忧虑消失了。此外,中国外交官近几年一直忙于解决与中亚各共和国及其他邻国遗留的边界争议。事实上,一种反向侵略正在发生:中国以人口迁移的过程缓慢占领西伯利亚部分地区。因此,中国追求海权,首先是一项指标,显示其陆地边界长久以来头一次不受威胁。滨海的城邦和岛国,无论规模大小,视追求海权为天经地义,而像中国这样在历史上闭关自守的陆地国家,追求海权多少显示出一种余裕,是大国崭露头角的标记。单从以广泛方式往海上发展来看,中国彰显出它在亚洲心脏地区称霸陆地的态势。没错,中国并不像十九世纪中期的美国那样,对自己周边区域有安全感,因为美国是名副其实的岛国状态。话虽如此,中国目前在陆地上的地位,比过去多数时候都更稳固无虞。
中国转向海洋的另一个因素是经济急剧蓬勃发展,导致贸易遽增,沿海商业的繁荣也随之而来。二○○七年,以货物装卸量来看,上海港口超越香港成为世界之最。到了二○一五年,中国将超越日本和南韩,成为世上最多产的造船业主。海权部分取决于商船运输,而中国将在这领域引领世界。
最重要的是,对能源的需求驱动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安政策:需要不停增长、不会中断的能源供应来维系经济的急剧成长。尽管中国愈来愈强调煤矿、生物能源、核电及其他替代能源,仍旧需要比以往更多的石油和天然气,也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同时,中国官方把进口石油产品这个需求,视为未来对手可能用来施压的罩门(对于能源来源多样化的需求,可以解释中国为何与苏丹这类的流氓政权公然交涉)。中国碳氢化合物的使用量比过去二十年高出一倍以上,在未来十年或二十年将要再高出一倍,自一九九三年起,中国的国内石油生产量一直处于停滞,于是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中国进口的石油和天然气大量(多达百分之八十五)从印度洋经麻六甲海峡,到达其太平洋沿岸各港口。从中亚经输油管进口的石油不敷使用;国内煤矿的用量不断增加仍未满足需求。特别是随着时间推移,中国会更依赖沙乌地阿拉伯的原油与伊朗的液态天然气。因此,它势必要捍卫环绕欧亚南部边缘区域的海上运输线。中国在古代是文明大国,近代却有深受西方殖民主义戕害的血泪史;因此,中国领导阶层怎么会把如此重要的捍卫任务,永远委托给自诩为全球海事公共疆域(maritime commons)保卫者的美国海军?若你是中国领导人,肩负把数亿中国人提升至高度依赖能源的中产阶级生活的责任,那么你也会发展可靠的海军,保卫横渡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商船舰队。
不过问题在于,中国领导阶层要发展出强大海军仍需要好几年。因此分析家詹姆士.穆尔维侬(James Mulvenon)认为,中国目前甘于搭美国海军对「公共财」提供的「便车」。注432然而,当中国海军能担负的责任愈来愈多,这样「搭便车」就变得没那么必要,美中的海军竞争就会开始白热化,尤其是美国自身舰队的规模缩减,两国海军在战备上的差距变小。
我们应该记住,自非洲向东到印尼,然后再向北至朝鲜半岛和日本,这个海上世界将日益成为一个广阔的连续体,因为各种运河和陆桥的修建计画在未来将会连接两大洋,而目前的通道仅限于麻六甲海峡、龙目海峡(Lombok)、巽他海峡(全在印尼海域,后两者与麻六甲海相比算是次要通道)。换句话说,欧亚沿海地区的地缘格局,注定会在某个时间点凝聚为一体。
这里将来也许会合为一个世界,但目前仍是两个世界,麻六甲海峡仍是一个伟大海洋文明的终点和另一个的起点。中国以内陆大国之姿趋向印度洋,在沿岸国家例如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和缅甸寻找出海口,因此与印度发生潜在的冲突;中国面向西太平洋有很长的海岸线,这使得它和美国之间也面临了潜在的冲突。
因此,让我们把目光从印度洋移往西太平洋。中国海军在中国战略家所谓的「第一岛链」上,只看到了麻烦和挫折,第一岛链北起日本和琉球群岛、朝鲜半岛的「南半部」,中接台湾,南至菲律宾、印尼和澳洲。以上各地除了澳洲外,全是随时会发生动乱的起火点。可能出现的局面包括:北韩瓦解或南北韩爆发战争;就台湾问题与美国开战;可以想见的海盗或恐怖活动,阻挠中国商船队进入麻六甲海峡和印尼其他海峡。为了东海及南海海床可能蕴藏的丰富能源,中国与邻国也有领海争端。在东海,中国与日本有钓鱼台(尖阁列岛)的主权之争;在南海,中国与菲律宾和越南就南沙群岛的一部或全部皆有主权纷争。特别是钓鱼台的争议,北京政府确实从中得到好处,随时视需要借此在国内挑起民族主义情绪,但在中国战略家眼里,这幅海景是非常严峻的。中国从太平洋海岸望向第一岛链,看到的是一道「逆向长城」,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詹姆斯.霍姆斯和吉原恒淑的话说:这是美国的盟国所布下一条严明的防线,等同以日本、琉球群岛、南韩、台湾、菲律宾和澳洲为守卫塔,潜在防堵中国进入太平洋。中国战略家看到这幅图景,对其海军被这样围堵非常恼怒。
以南北韩为例,如果两韩统一,起码在地理上而言对中国不利。朝鲜半岛从亚洲大陆远远延伸出去,控制着中国东北的海上交通,更明确地说,把中国最大的海上油田渤海夹在它腋下。此外,统一的韩国会是民族主义的韩国,对于历史上曾占领过它的强大邻国(中国和日本)怀有明显的矛盾感情。短时间内朝鲜半岛的分裂对中国有利,因为虽然北韩政权令人摸不透而使北京头痛,但它在中国和南韩这个活跃、成功的民主政体之间形成缓冲。
至于台湾,则说明了世界政治的基本事实:在道德问题表象之下往往是权力问题。各方讨论台湾问题都是从道德角度出发,不问其主权的归属就地缘政治而言至关重大。中国谈到台湾,都说是巩固它的固有疆土,要为全体中国人的利益而统一中国;美国谈到台湾,说的是维护民主典范。但台湾还具有别的意义:用已故麦克阿瑟将军的话来说,台湾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占据中国凸出海岸的中心点,像美国这样一个外来大国,可以从台湾向中国沿海外缘「辐射」力量。如此一来,没什么比台湾实质上的独立,更能让中国海军谋略者发愁。在这逆向海上长城的几个守卫塔中,台湾可被比作最中央、最高的一座。台湾如果回到中国怀抱,海上长城及其代表的海上链条就断裂了。
中国渴望拥有一支真正的蓝水海军,或者说海洋海军,就像美国曾拥有过的。为了建立一支蓝水海军,美国首先不得不藉由向西部扩张和移民拓荒,以此巩固北美大陆的温带地区。假使中国成功巩固台湾,那么其海军不仅能突然间在第一岛链居于有利的战略地位,同样戏剧性的是,它的国家能量也会大大释放出来,向外辐射的力量将达到目前所无法想像的程度。当台湾问题转向对中国有利的一面,那么中国将会如霍姆斯和吉原恒淑所设想的,更无所拘束地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寻求海军大战略(假若中国能在最西边省分新疆,更有效地巩固汉族对说突厥语的维吾尔穆斯林的控制,也会更鼓舞它在泛海洋领域内的海军行动)。
中国决意拿下台湾的可能影响,起码在象征意义上,类似一八九○年印地安战争的最后重大战役──伤膝河大屠杀(Wounded Knee Massacre)。 「蛮荒西部」在那惨烈事件后被兼并,美国军事开始热切向海洋聚焦,并于十余年之后开始修建巴拿马运河。虽然「多极」这个形容词被大量用来描述全球局势,但唯有台湾和中国大陆合并在一起,才是这种多极世界真正出现的标志。
中国奋力不懈地试图从各方面(主要是经济方面)突破美国主导的第一岛链。像菲律宾和澳洲这类国家会把中国视为首要的贸易伙伴。以菲律宾为例,美国从百余年以前在那遗留的事物有:战争、占领、长达数十年的政治干预和大量的经济援助。而今中国正竭力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几年前甚至向菲律宾提供了联防协定,其中包括一项情报共享协议。因此你不得不想像未来的情况:日本重新发展武备,南北韩统一而且民族主义高涨,台湾就作用上而言与中国是统一的,而菲律宾和澳洲在名义上亲美,但因为贸易加上中国经济和军事持续崛起相关的其他现实,所以倾向中立。结果,随着美国力量逐渐衰落,而中国在所有海防前线突围,西太平洋情势更加不稳定。
在这种局面里,向东,中国开始计画突破由美国领土关岛和马里亚纳群岛等形成的第二岛链。实际上,中国已经在整个大洋洲地区快速发展自己的利益,与许多看似不起眼的小岛国广泛加强外交和经济联系。
但中国海上利益最显著的区域在南方,也就是印度洋和太平洋交会处。这片南海及爪哇海的复合海域,由新加坡、马来西亚半岛、菲律宾南部数千座岛,以及特别是印尼群岛所掌控;中国通往石油丰富的中东及非洲的海路交通,在这片海域的风险最高。这里有基进的伊斯兰、海盗和崛起的印度海军,况且印尼各海峡都是严重壅塞的地理瓶颈,却是中国大部分油轮和商船队的必经之路。这里还有许多中国想开采的重要油田,因此一些分析家判断,南海将变成「第二个波斯湾」。综合这些因素,加上中国战略家从中看到的机会、问题和噩梦,使得印度洋东边门户的这个区域,成了未来数十年最关键的海域之一。就像一个世纪前美国海军前进加勒比海海盆并控制该海域,中国海军也必须前进南海,就算不能控制也要跟美国一样,在这片海域取得主导地位。因为麻六甲海峡可以比作巴拿马海峡,同样是通往更广大世界的门户。
在二十世纪中期,荷裔美籍的地缘政治学者尼古拉斯.斯派克曼(Nicholas Spykman)曾指出,综观历史,每个国家都会致力于「周边和跨海扩张」,以便控制毗邻海域:希腊试图控制爱琴海、罗马试图控制地中海、美国试图控制加勒比地区……按照这逻辑,中国也会试图控制南海。
作者为美国资深记者、地缘政治专家、旅行作家。过去三十年间,他担任《大西洋》(The Atlantic)月刊记者,撰述可见于《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等重要报章杂志,观点经常引发相关政治、媒体、学术界讨论。他也曾担任美国智库战略预测公司(Stratfor)地缘政治分析主任、美国海军学院(United States Naval Academy)客座教授、五角大厦国防政策委员会(Defense Policy Board)委员、华盛顿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资深研究员。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两度将他列入「全球百大思想家」之林。卡普兰曾实地采访中东、两伊战争、巴尔干半岛、前苏联与阿富汗战争等战略要地与新闻前线,至今已有十数本关于外交事务、地缘政治及旅行相关书籍。在台出版作品包括《世界的尽头》、《南中国海》、《地理的复仇》、《欧洲暗影》、《重回马可孛罗的世界》、《西进的帝国》等书。
相关著作:《重回马可孛罗的世界:战争、策略与二十一世纪的欧亚大陆新变局》《西进的帝国:地理如何形塑美国的世界地位》《欧洲暗影:一段横跨两场冷战、三十年历史的东欧边境之旅》
书名:《季风亚洲:二十一世纪大国赛局与地缘政治的冲突核心》
作者:罗柏.卡普兰(Robert D. Kaplan)
出版社:马可孛罗
出版时间:2021年11月
——思想坦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