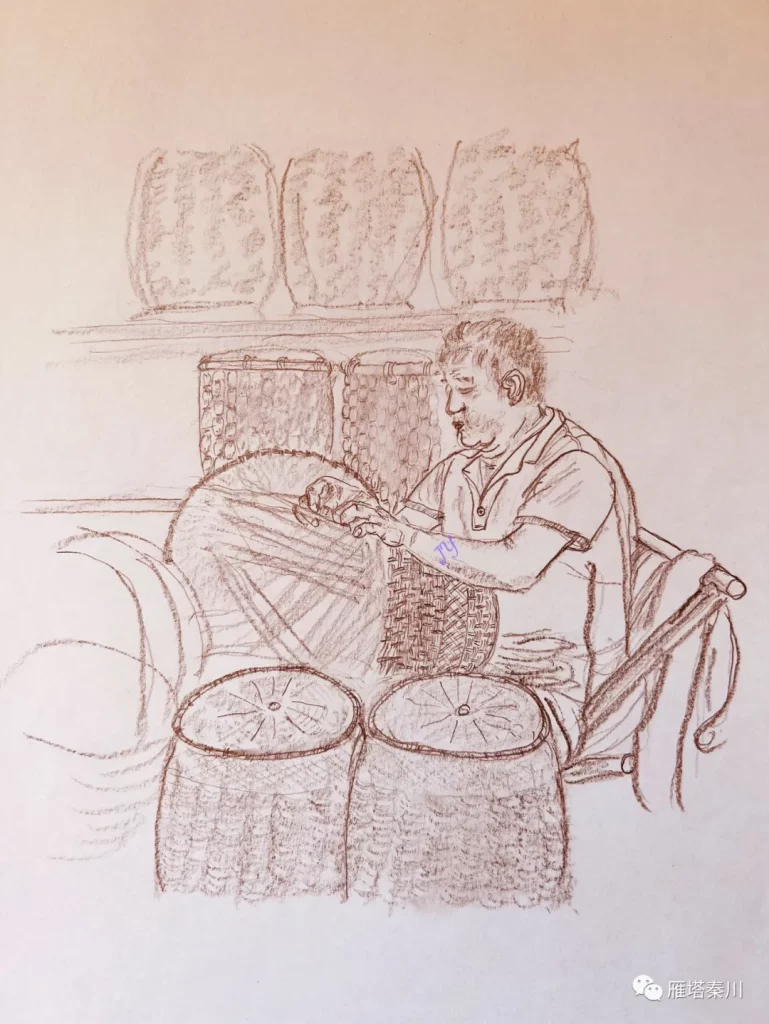Original 28rcm 雁塔秦川 2022-02-08 18:07
【法家杂论】之一
商鞅与赵高,是秦史(统一前的秦国与统一后的秦朝)上最有名的人物之二,通常也被看做是正反两面的极端。不论是过去人们的“诛暴秦”,还是今天流行的“大秦赋”,无论人们对秦是好是恶,对于商鞅有大功于秦,赵高有大祸于秦,似乎都没什么争议。
而在这两人的行为中,最有名而且无争议或很少争议的大概就是商鞅的“徙木立信”和赵高的“指鹿为马”了。
“指鹿为马”堪称遗臭万年。史曰:
(赵高)“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或言鹿者,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后群臣皆畏高。”
赵高拉着一头鹿上殿,硬要满朝大臣说是马,谁敢讲真话,说这明明是鹿,就要被他加罪陷害。这逼人昧着良心说假话的“指鹿为马”之恶,是从古至今没有人替他争辩的。
指鹿为马雕塑
尽管过去也有些文人猜测“赵国人”赵高祸秦,是有意辱身陷敌为赵国复仇,“指鹿为马”也被说成“报赵倾秦”的壮举,甚至称颂“鹿马计胜长平战“,“赵高功冠汉诸臣”,“留侯椎铁荆卿匕,不及秦宫一赵高,”但这是说他有功于赵(其实也是无稽之谈),就秦国而言赵高是祸害,仍是没有问题的。
而商鞅就是个争议很大的人。有人夸他是中国最伟大的改革者,有人骂他是作法自毙(这个成语就是从他而来)不得好死的厚黑学家。有人说他造就了“强秦”,是大一统的功臣;有人指他为“暴秦”的鹰犬,是辱民弱民的罪魁。不过,商鞅的言行有许多。他的不少主张听起来就让人起鸡皮疙瘩,如什么弱民、辱民、贫民、愚民、政作民之所恶不作民之所乐、乃至以奸驭良、什伍连坐等等。但也有些言行颇得后人好评,其中最著名的,大概就是所谓“徙木立信”之举。就连一些批评秦制的人,也觉得他这一招很出彩。史称:
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这个故事是说商鞅要做些通常让人难以置信的事,害怕老百姓反对。——请注意,不少人声称反对“商鞅变法”的只是贵族,老百姓是拥护的。可是太史公明明说的是“恐天下议己”、“恐民之不信”,这“天下”和“民”不会只是贵族吧?
照理说,既然大家对你难以置信,你就该做几件好事让大家看看,好争取民心?可是商君大人不这么想。也是啊。商君又不是民选总理,用不着在乎选票、讨好民众。相反,商君书中充满仇民憎民蔑民的话语,甚至主张“政作民之所恶,不作民之所乐”,我就是要做百姓痛恨的事(当然,得是皇上高兴的事),而绝不做百姓高兴(皇上或许不高兴)的事!所以你想,商鞅会在乎百姓的信任吗?他只要百姓服服帖帖——所谓“立信”,并不是信任,而是相“信”我什么都做得出来,从而只能无条件屈从于我。
那么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商君的妙计是:你们不是怀疑我的做法违背常理吗?我就偏要做一件最不合常理的事让你们看看!
“徙木予五十金”之不合常理,是大家都知道的。问题是:今天很多人无法想象其荒唐乖戾的程度,总是想把它解释得稍微合理、至少荒谬程度小一点——可见大家的“觉悟”还不够高啊。当年L不是说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吗?如果太荒谬,执行中还是理解不了怎么办?
于是今人往往会把“徙木”的难度放大,而把“五十金”的价值缩小。
比如有人说,这里的“金”不是真金、黄金,而是铜;还有人说这“五十”不是五十斤,而是五十两,甚至只是五十铢。这当然是不经之论。战国秦汉间黄金不仅“为币”,而且当时还严禁“伪黄金”,以铜鎏金作伪要处严刑,甚至黄金成色不足都有惩罚。金铜不分怎么可能?当然,金铜既然都是货币,等价(绝不是等重)的黄金与铜币是可以互兑的(常引的汉价是“一金万钱”)。秦汉史籍中确有以金计值而实际以官定兑价付给铜钱的记录,但是商鞅此举并无这种迹象。就算有,这种等价兑换也不影响其赏额惊人到不可思议的程度。
更清楚的是那时金衡通常称镒、称斤,而绝不称两。史记注引臣瓒曰:“秦以一镒为一金,汉以一斤为一金。盖汉以前以镒名金,汉以後以斤名金也。镒者二十四两,斤者十六两也。”《汉书.食货志》也说:秦时“黄金以镒为名”。除了24两为一镒外,史载还有20两(赵歧)、30两(郑玄)为一镒之说,总之一镒比一斤更重是无疑的。而黄金称两,则是东汉以后尤其近古才流行的——这就是经济史上有名的“汉金消失之谜”。近30年前我就在《历史研究》上长文详论过此事。学界前贤,如彭信威先生早在民国时期的《中国货币史》上也论及于此,当代学者如胡珠生、李祖德、杜劲松等也屡论之。所以,太史公记述商鞅重赏“五十金”应当是秦时的五十镒黄金。但为了保护读者的下巴不被惊掉,姑且少算一点,权当做太史公时代的汉制五十斤吧。如果不能证明太史公是昏了头乱写,那“五十金”至少也得是50斤(时衡)黄金,断不能强做他解。
除了贬低赏格,还有更多的人是加大“徙木”的难度。太史公文中明明说的是“国都市南门、北门”,后来却被有的人想象成国都的南、北门,事情就显得不那么荒谬:把三丈之木(按现在的尺度,3丈就是10米长,似乎不是个小木头)从城南搬到城北,听起来还是挺费力的。给10斤黄金(尽管当时的斤也只有今斤的一半重,10斤黄金还是很惊人了)的重赏虽显过分,好像还不是太荒唐。
于是我一查,今天几乎所有“颂秦褒鞅”的影视、画作,都把这事描绘成在高大的城门下立着根又高又粗的巨柱,搬动它好像挺难的样子。
“徙木立信”
但是,扛起这么重的木头从南到北穿过整个都城这么长的路,为什么初时百姓连这十斤之赏都不信?难道秦廷的信用已经破产到如此地步了?商鞅入秦之前,秦的动员力就那么不堪吗?
要知道,秦国并不是商鞅执政后才成为强国,早在春秋时的秦穆公就已跻身“五霸”,商鞅之前作为战国七雄之一的秦又比春秋时更强,只不过还无力一统天下而已。如果商君入秦之前,秦人都不把朝廷的话当回事,国家动员力几为零,在战国背景下秦还不早就被灭掉了,它怎能长期成为强国?
略加考辨就明白了:其实这次国人之所以开始不“信”,就因为商鞅此举在常人眼里实在太匪夷所思。首先,当时度量衡不同于现在,先秦的一丈约当今丈之半强,若长宽高之比不变而取立方比,“三丈之木”的体积、重量仅约相当今天概念的八分之一,对男子汉而言应当不过是根随手可移的木杆而已。
其次,所谓“国都市南门”决不能妄删一字,当成国都南门。明显地它并不是城门,只是“市门”而已。要知道,当时不像宋代以后城里才有的街市,先秦时城里做买卖的地方只是一个或几个“市墙”圈起来的市场,日中为市,定时启闭。后来唐长安的东西二市和汉长安的九市,就是历史上“闾市”之极,其实也没多大,何况先秦。
更何况,商鞅执政之初的秦都并不在后来的秦咸阳,而在规模很小的栎阳城。加上秦历来只重“耕战”,以商为“蠹”,买卖人都被打入“市籍”视同贱民,因此栎阳小城中的“市”不会比今天县城里一个农贸市场大多少。对一个壮汉来说,把一根不重的木杆从市场南头移到北头,比“吹灰之力”也多费不到哪里去,就这能值10斤黄金之赏?你当这是持戈陷阵杀敌斩将啊?
太过荒唐,无怪乎没人信了。
而无人相信之际,商鞅居然又把重赏一下提高五倍,达到黄金50斤——很可能还是五十镒,即相当于今天13-25公斤,就算秦汉“多金”而后世不及,这么一堆黄灿灿的金子也太吓人了吧?吓人到什么程度?我给你联想一下:秦汉都有战场上斩首赐爵且爵可定价之制。秦的价码无考,西汉的价码相当于斩首一人值十七金(中井积德据《平准书》考)。假设“汉承秦制”,那就相当于把这木杆儿在市场里挪个位置,等于在两军相搏你死我活的战场上连着斩杀三个敌军,这是连晋三爵的大功啊!
拿个木杆穿过市场就连晋三爵?这是什么意思啊?
不就是显示“权力万能,我大权在握,什么荒唐事我都做得出来,你们服不服?!”
果然,有个愣小子拿起木杆,大步流星就从市场这头走到那头。人们正等着看笑话呢,不料商鞅立即兑现,真的给了愣小子50斤黄金!愣小子狂喜之余,秦民无不惊掉了下巴:乖乖,这公孙鞅大人果真是权力万能啊,这么荒唐的事,他就是做得出来,服了服了!
后来据说公孙鞅用这一手真是驯服了秦人,绝大多数秦人丧失了思考和判断能力,就像《商君书》所主张的“愚民”(“民愚,则知可以王”),成了指哪打哪的机器。公孙鞅就此立下盖世之功,受封成了商君。但几年后,商鞅在秦制内的党内斗争中失势。落荒而逃又撞在自己立下的锢民苛法中,“作法自毙”。如此暴秦功臣,竟被五马分尸而惨死。
然而,秦民经商君“蒙启”之后,已经习惯于服了服了,对此绝无异议。于是商君虽死,秦制益张。
直到后来出了个赵高,他“指鹿为马”,什么意思?不也就是显示“权力万能,我大权在握,什么荒唐事我都做得出来,你们服不服”吗?
当年那个愣小子带头服了服了,立得重赏。后来绝大多数人都服了服了,当权者指鹿为马,那就是马吧。当年愣小子拿个木棍招摇过市,你都可以当成挺抢持戈杀敌陷阵般受彼重赏,那今天这鹿,为什么就不可以当成长了角的小马呢?但是商鞅做的似乎还不彻底,仍有些人不服不服,说这明明是鹿呀,怎么可以当成马,就像当年持棍过市,怎么能当成持戈陷阵呢!结果,赵高“阴中诸言鹿者以法”——史书说得很清楚,赵高正是用“法”(就是商君之法吧)将他们都杀了。于是“后群臣皆畏高”。
总之,两人及两事都是要让大家明白权力任性可以无极限,只要我掌权,无论多么荒诞也必须听我的。不同的似乎仅仅是:商鞅赏顺而赵高罚逆,异止此耳。
不过其实也谈不上异,因为商君自己就是明确主张重罚更胜于重赏的。治国要“重罰輕賞”,决不能“重賞輕罰”,语见《商君书. 去强》篇。他举例说,老百姓或许不爱钱,但都怕死。再胆怯的兵,你抡着大刀在后督战,不冲锋就杀头,他也能豁出来。等他冲上去了,再赏他俩钱,他就习惯卖命了。假如反过来,他缩头缩脑时你用这俩钱让他冲锋,他能干吗?所以慈母必出逆子,孝子那都是棍棒打出来的!仁君对老百姓好了,百姓就会漫天要价甚至犯上作乱。只有暴君下狠手,把百姓的脊梁骨给打断,他们才会乖乖听话。因此,善治国者就要“政作民之所恶”,而绝不“作民之所乐”!
《商君书》
那当初为什么又要重赏徙木者呢?没办法,那时百姓还不知我商君的厉害,大家都觉得徙木十金荒唐,不愿去拿那木杆,我总不能把他们都杀了吧。但后来我以重赏开路,让大家都服了服了,对那不服的“一小撮”当然就必须下狠手了。
所以,“徙木立信”与“指鹿为马”原本一脉相承,那赵高其实也不过是秉承商君遗教,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发展了商君的做法而已。
其实按史书明载,赵高也确实是商君的出色后学。《史记··蒙恬列传》称:“秦王闻(赵)高强力,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高既私事公子胡亥,喻之决狱。”又《李斯列传》载赵高自称:“高,固内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笔之文进入秦宫,管事二十余年。”原来,赵高当年就是因为“通于狱法”被秦王政(后来的秦始皇)慧眼识“猪”,把他从太监“厮役”之贱,破格提拔成大内总管的。他作为刀笔之吏,在商鞅开创的“以吏为师”道路上飞黄腾达,不仅“管事二十余年”,还真的在宫中当起了胡亥(后来的秦二世)的老师,“喻之决狱”——教他学法家的学问。前面说过,对于不承认“指鹿为马”的人,他也正是用法家那一手来陷害的。
近年李开元先生大申前已有之的异论,为嬴政与赵高做了许多辩白。他说赵高不是太监,已有学者力驳其非。但他说“赵高堪称精通法律的专才,有家学渊源的法学名家。晚年的秦始皇将少子胡亥的教育委托于他。”如果所谓法学指的就是法家商君之学,那李开元之说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可见商鞅与赵高,实为一丘之貉。怪的是颇有人褒鞅而贬高。今天有人居然说,商鞅“徙木立信”是“树立了法律的权威”,这样说的人好像还很多。我就百思而不解了:“徙木立信”与法律有什么关系呢?无论是恶法还是良法,但凡法律都是要能常态实行的。商鞅后来确实立了许多苛法,包括最后令他“作法自毙”的禁徙法,无论好恶那总还算是法。但“徙木立信”能是立法吗?秦人如果个个都可以拿根棍子招摇过市就能向国家要50斤黄金,那秦国还不立即财政破产啊?就像赵高指鹿为马,你当他真认为鹿就是马,会立个法让秦国骑兵全都骑鹿打仗么?
商鞅与赵高
其实徙木立信也好,指鹿为马也好,都只是一次性的淫威展示;商君也罢赵高也罢,都不会以此作为法律,而只是显示一种“我想怎样就怎样”的无限权力傲慢与极度砖制任性而已。无论权力的言行多么荒唐乖戾,多么违背常识,你“信”了(其实应该说是屈服了)就重赏五十金,不信就“阴中以法”杀你没商量。而且权力可以翻云覆雨朝三暮四(这就叫“变法”),无法以情理度之,今天他可以徙木赏金,明天就可以触木斩首;今天可以指鹿为马,明天就会指良为奸, 看你服不服?
所以,徙木立信与指鹿为马这种荒唐事越多,这个国家离所谓的法制(无论是约束权力以保障公正的现代法治,还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古代理想)就越远。这甚至都不能说是“恶法亦法”。因为无论良法恶法,只要是法就必须常态实行,不能只是一次发威把人唬住就完了。
虎年大吉,开工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