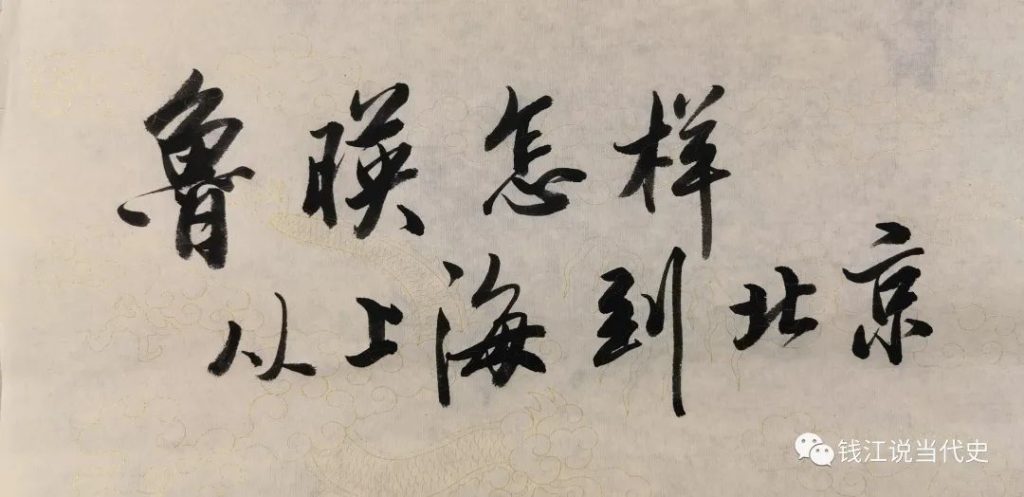鲁瑛(1927—2007),革命战争年代的《渤海日报》编辑、山东《大众日报》编辑、记者组组长,后调上海《解放日报》,担任驻山东记者站负责人、《解放日报》总编辑办公室副主任、党委办公室主任。
“文革”爆发的1966年6月作为“中央工作组”进入人民日报领导层,此后担任人民日报主要负责人8年之久。文革结束后即接受审查,被开除党籍,80年初结束审查恢复工作,在人民日报出版社担任编辑。
本文主要依据对他和家人的采访,和其他知情者提供的情况,包括部分文书档案。
接前文:
1963年,姚文元调到《解放日报》文艺部。这个人性格特别,很少和别人搭话,总是呆在自己的屋子里埋头编稿或写作,报社的许多人不认识他,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鲁瑛在这时和姚文元相识了,很少对话。但是鲁瑛知道柯庆施、张春桥很看重这位姚文元。姚文元来解放日报担任编委,参加编委会议。鲁瑛也是编委,在一起参加会议就认识了。在鲁瑛记忆中,开会的时候姚文元从来不发言,就好像会场上没有这个人。渐渐地,他连报社也很少来了。
鲁瑛没有想到文革中到北京以后,和姚文元的交道越打越多,因为姚文元渐渐成了顶头上司。
这张文革初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开大会时拍摄的照片中,左起: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
1965年,根据华东局的指示,《解放日报》组织力量采写山东黄县大吕家公社下丁家大队发展农业生产的事迹。黄县是鲁瑛的家乡,报社委派鲁瑛带领华东新闻部记者方远、新近大学毕业到解放日报当编辑的周瑞金和摄影记者赵立群,加上《大众日报》记者李彦臻,联合采访后写成长篇通讯《下丁家人创业之路》,配发评论发表,引起了很大反响。采写这篇通讯,鲁瑛是带队领导,出点子,审阅初稿,不再是主要执笔者,然而文章发表时署名在前。(2012年7月19日下午电话采访周瑞金的记录)。
1965年4月,鲁瑛(左2)、方达(左1)、周瑞金(右2)在山东蓬莱仙阁
8. 突然受命去北京
1966年6月初的一天,可能是6月2日,最晚是3日,时任上海解放日报党委委员、党委办公室主任鲁瑛接到电话,说总编辑、党委书记马达找他谈话。
鲁瑛马上走进了总编辑办公室,马达很郑重地对鲁瑛说,根据市委的决定,借调你和邵以华到北京《人民日报》去工作,因为那里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要搞‘文化大革命’,有很多干部跟不上形势,不能工作了。这样一来,人民日报很需要人,中央就要我们上海支持,调干部参加对人民日报的领导,市委决定调你和邵以华两人马上就去。从目前来说还是借调,你们到北京去,家属不去,孩子也不去。至于以后怎么办,待以后再说。
这时,鲁瑛还主管着报社的华东新闻部,工作压力不轻,他回忆说:“我看马达对我说这番话的时候,语气是非常肯定的,表明这是上级的决定,丝毫没有征求意见的意思。我就当场表示,接受组织安排。”
马达马上吩咐说,你们明天就走,只带组织关系。
马达找鲁瑛是单独谈话,随后还和邵以华谈话,估计是同样内容。
当时,对北京发生了什么,鲁瑛并不知情,他当时比较关注的还是上海和华东地区事态。不过,他已经认真阅读了《人民日报》6月1日的头版头条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感觉这篇社论“来头”很大(但不知道这是陈伯达改定的标题和文章)。从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海瑞罢官〉》到此时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半年以来国内政治局势急剧动荡,他感觉这次运动的规模将是巨大的。
事后鲁瑛得知,就在大约3天前的5月31日晚上,陈伯达带领“中央工作组”进入人民日报社,夺了总编辑吴冷西的权。工作组由陈伯达挂帅,主要助手是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穆欣,工作组成员还有钱抵千(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朱悦鹏(《解放军报》党委委员、记者处处长)、尚力科(《解放军报》党委委员、军事工作宣传处副处长)、杨丁(《红旗》杂志社编辑)。另从上海抽调2人,名单待定。
空缺的两人由上海《解放日报》抽调,此事由中央通知上海市委。后来,鲁瑛听代理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唐平铸说,中央原先要调的是《解放日报》总编辑马达。但这时上海局势已不太稳定,马达又是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特别倚重的“笔杆子”,陈丕显不同意放他走。马达也不想到北京去,因为首都风云已经变幻不可捉摸。于是在第二选择中选上了鲁瑛和邵以华。
这一去波诡云谲。
20世纪60年代,和采访对象在一起的鲁瑛(右)
9.初到人民日报的鲁瑛
和马达分别谈话后,鲁瑛和邵以华马上到上海市委组织部转党组织关系。第二天两人乘火车前往北京,6月4日到达,被一辆小汽车接到王府井大街上的人民日报社招待所。
《解放军报》代总编辑唐平铸在5月31日晚上跟随陈伯达到人民日报“夺权”,随即像是“中央工作组”成员的样子,主持人民日报日常事务,他单独找鲁瑛谈话,表示欢迎他来人民日报。
唐平铸对鲁瑛说,你写的东西不错,以前写的山东下丁家大队的典型报道我认真地读过。我们已经研究了你的工作,还根据你在解放日报的工作情况,安排你主管人民日报的记者工作。将安排邵以华负责行政后勤工作。
当天,鲁瑛和邵以华在人民日报招待所同住一屋。第二天,他们前往中组部转了组织关系,但是两人的工资关系还在上海解放日报。鲁瑛的妻子张文卿每月向北京汇出生活费,她要到几年后才调到北京。
当时,鲁瑛是行政15级工资,每月130元;妻子工资不高,加上对老家还有一些负担,全家人花销相当紧张。鲁瑛前来北京的时候没带多少像样的衣服,以致于接待了几次外宾以后,外交部礼宾司官员提意见说,人民日报的鲁瑛穿得太差了。但那时鲁瑛确实没有什么好衣服。
到北京后不久,“检阅红卫兵”的大潮涌来,鲁瑛负责组织记者们采访。8月的一天,他也穿上绿军装上了天安门,就站在距离领袖毛泽东不远的地方。
那天,有一阵子毛泽东和焦裕禄的女儿在一起,毛泽东看到了鲁瑛,觉得不熟悉。
这天毛泽东离开天安门城楼的时候,当时没有电梯,是走下来的,鲁瑛站在一边,又被毛泽东看到了,问:“你是哪里的?”
鲁瑛回答说:“我是人民日报的。”
毛泽东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说:“我叫鲁瑛。”
毛泽东就说:“哦,我不认得。”
这就是鲁瑛和毛泽东的第一次近距离直接接触,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这样近距离地讲话。
来到北京,狂飙飞卷,鲁瑛只见人民日报的领导席上没有常客,来来往往走马灯一样。后来他说,读到鲁迅的诗:“墙头变幻大王旗”,觉得很像他刚到北京时的情况。
他还告诉本文作者,解放日报的总编辑魏克明的工作作风给他很大影响,所有文书档案及时整理,分门别类归档,妥善保存。来到了北京,他也这样做。在这方面,鲁瑛相当仔细,结果是很得益的。
进入1967年1月,风云变化,代总编辑唐平铸的地位不稳,1月中旬就被“揪”了出来,靠边站接受审查。
1967年1月6日的中央文革成员,左起:戚本禹、陈伯达、江青、唐平铸,他们来到新华社讲话。画面上是陈伯达在讲话。仅仅一周之后,唐平铸就被“揪”了出来,停职审查。
原先“中央工作组”的成员中,来自红旗杂志的杨丁早就不见踪影,来自军报的也纷纷归去,到后来只剩下从上海来的两人了,鲁瑛又是其中唯一编辑部门出身的干部,他具有的“山东革命大学新闻系”学历在当时已经相当过硬了。
唐平铸受审查停止工作,使鲁瑛在报社事务中更多地负起责来。他和中央文革中先后分管报纸宣传的王力、姚文元的交道和接触也越来越多了。
到北京以后,鲁瑛很想回上海工作,但几次想提出来,都因当时突然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打消了念头,直到最后也没有回到上海。他的后半段人生悲剧,就此拉开了大幕。
退一步来说,来到北京,进入人民日报,鲁瑛本人有错吗?应该说没有,如果有的话也不应该由他来负。但这确是鲁瑛人生悲剧的先导,在此之后的年月里,他在悲剧深潭中越陷越深,其中必有要由他自身承担的责任。
(本文告一段落)
(2012年4月改)
2022年7月10日订正
对于鲁瑛的早年经历,曾以《鲁瑛是怎样从上海到北京的》为题发表于 2010年第1期《世纪》杂志。以《鲁瑛人生中的红色前半程》为题发表于2013年5期《党史博览》杂志。
本文有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