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下引此篇说好文章「须有大问题、大功夫、大智慧」,列举史地大家谭其骧,黄河治理自然算大问题,但是四九以后,黄万里硬是跟毛泽东共产党说不清楚这大问题,要害是自然力量非人力可以抗拒,对于信奉「人定胜天」的唯物主义者乃对牛弹琴,而令中华民族千年恐惧洪水的黄河,竟然间歇性断流,这种荒谬,也随着中国崛起,而毁伤大好河山,江湖枯竭,海滨翻红,雾霾盖顶,森林消失,人民罹癌,大自然的报复冷酷无情,江山社稷一并陷落。我写黄河时,读到两位「大智慧」,黄万里、谭其骧。 】
黄万里尝言,凡河流的上游必然遭冲刷,下游则出现淤积;「这是指一长段河流经过相当长的时程而言,分析用的是统计法。」这当然是水文科学。黄河之事,尤其泥沙与洪水的关系,非长程历史说不清楚(「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史学家谭其骧以他的渊博,早在1962年就从史地角度论证了这一点。
问题起于「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原因何在?近世史家皆言,「千年无患」,功在王景。谭其骧却不苟同,质疑一次「治导」工程何能「功垂千载」?他认为说通这件事,对整个中国历史都很重要。
谭其骧是史地大家,他循上游土地利用方式的思路,从畜牧、农耕对水土流失程度的区别,梳理锁定山陕峡谷流域和泾渭北洛上游,对黄河下游水患最关紧要,并举史料追述这两个地区千年以来的「人类踪迹」:战国以前那里是畜牧区,农业很微弱,主要是涉猎活动。 「这两个地区与其南邻关中盆地、汾涑水流域在地理上的分界线,大致上就是当时的农牧分界线。」他透视历史,可达致如此细节:晋西北在春秋时代,尚产名曰「屈产之乘」的骏马;直至西汉,善射骑的名将多数出身那里。秦汉两朝为逐匈奴而「戍边郡」,「募民徙塞下」,大规模移民的目标正是上述两地区。 「先为室屋,具田器」,汉族到哪里,农业就到那里,而且那里「地肥饶」,边陲竟成「新秦中」。另外,秦汉还以「实关中」的政策,加强中央集权,关中盆地的边缘「云阳」「云陵」,都在泾水上游。 「此二地区从此以畜牧射猎为主变为以农耕为主,户口数字大大增加,乍看起来,当然是件好事。但我们若从整个黄河流域来看问题,就可以发现这是件得不偿失的事……,这一带地区的大事开垦,结果必然会给下游带来无穷的祸患。」汉武帝以后,黄河下游的决徙之患遂越闹越凶。
东汉王莽重开变衅,汉家放弃缘边八郡,匈奴「转居塞内」,变农为牧。黄巾起义后,「百姓南奔」、「城邑皆空」,边陲成清一色的羌胡世界,蔡文姬的《悲愤诗》称西河故地「人似禽兮食臭腥」。东汉以降,「历史上的魏晋十六国时代是一个政治最混乱、战争最频繁的时代,而在黄河史上的魏晋十六国时代,却偏偏是一个最平静的时代。」从此,农牧分界线南移至黄河中游,大致东以云中山、吕梁山,南以陕北高原南缘和泾水为界,东南是农区,西北是牧区。这条分界线,直到北魏后才打破。之前黄河有五百年安流。再加隋唐三百年,情形虽破碎而纷杂(隋末离乱、安史之乱前后),黄河算是基本安流,河患远不如西汉。由此可见,汉家靖边,则黄河多事;匈奴南下,则下游安流。农耕与游牧的拉锯,竟有如此非预期后果,天道实非人力可为。
谭其骧旨在「古为今用」,结论指出:「下游也不可能单单依靠三门峡水库就获得长治久安。因为三门峡水库的容积不是无限的,中游的水土流失问题不解决,要不了一百年,泥沙就会把水库填满。」
——摘自《屠龙年代●黄河史二:读谭其骧》
—作者脸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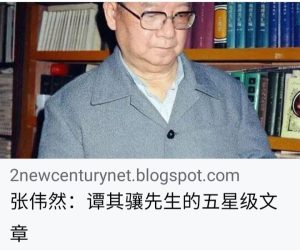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2/08/blog-post_703.html?spref=fb&m=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