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惠敏 2023年06月18日 来源:上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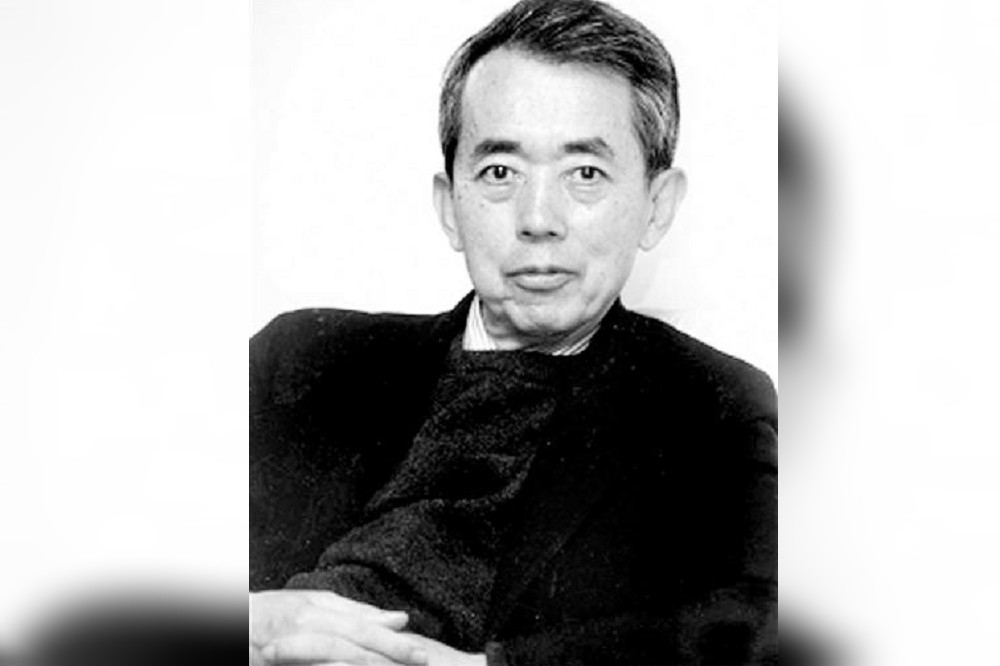
张光直的抱负是想要融入中国考古事业,但在他漫长的追求学术交流的过程中,他的「中国梦」却成了他生命中的一场梦魇。 (图片取自网路)
《余英时回忆录》(允晨文化2018)花了相当的篇幅谈论他在美国的两位挚友高友工和张光直。他和张光直的友谊始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当时他是以香港新亚书院访问学人的身份抵达哈佛大学,访问期满后改为研究生身份攻读博士。张光直则是台大考古人类学系的杰出毕业生,大学时代属于台大校园中的左翼,在「四六事件」中曾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大学毕业后经中研院史语所所长李济推荐,赴哈佛读研究所。对于张光直的的待人诚恳,治学勤奋,严于律己,余英时在回忆录中着墨甚多。但他也坦承,两人在对待中共的态度上,是泾渭分明的。
余英时的立场是绝不认同中共的极权政治,但他对大陆的学术界并无偏见。张光直则是从早年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倾心而认同祖国,同时不断期望他的毕生志业,尤其是在考古发掘方面的热忱,能为中共学术界所接受,将他视为「新中国」考古事业的一份子,一个自己人。张光直在台湾中研院副院长任内(1994-1996)推出他在人文学科方面的改革计划而受挫时,他不免怀疑余英时是否出于不同的政治理念而从中作梗。余英时在回忆录中也花了篇幅来为自己澄清。
张光直的改革计划是把考古组从历史语言研究所分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考古研究所。他的构想是这个新所的研究人员人数要多达一百人,可与大陆匹敌,在研究领域上与大陆的考古所互通声气,并以大陆的发掘工作为主体。问题是,在台湾成立如此庞大的考古队伍是否切合实际?涉及多大的经费开支?以大陆为主体的构想,在当时李登辉主政的台湾政治环境中行得通吗?张光直的计划案果然很快就遭到史语所领导层的否决。
另外是张光直打算重组文哲所,延揽一位大陆统战部支持的台湾学者,作为一个领导人选,但由于未能通过中研院聘任程式中的专家评审和咨询委员会审核这两关,他的构想最后也胎死腹中。张怀疑余英时作为文哲所咨询委员,是否在评审方面发挥了什么「影响力」。余英时当时人在美国,他在回忆录中表明他自始至终都不知此事。
回到历史上看,张光直这个「祖国」发烧友,1973年就修书致郭沫若,期待以个人的身份回国参加考古工作,并将此信副本连同另一私函寄给考古所所长夏鼐,但两封信都石沉大海。张光直第一次到中国是1975年随同美国的古人类学代表团去访问的。在访问期间,他仍不死心,要求与夏鼐「个别谈话」,提出希望到考古所工作的要求,但夏鼐的反应是「不置可否」。后来张光直一有机会就反复提出这个要求,也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的回应。
为什么?
余英时叙述张光直这段经历时,不免为挚友叫屈。无论如何,张光直在美国考古人类学界不仅成就非凡,也是国际知名的人类学家。这样的人才甘愿放弃哈佛教职,到大陆参与考古工作,按常理,实无理由拒绝。论出身,国民政府时期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实习生起家的夏鼐,自己也曾到英国读博士,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在这方面不能说缺乏见识。

张光直于 1997年,河南商丘,手拄拐杖,由人搀扶着考察东周时期的夯土城墙。 (作者提供)
夏鼐拒合作
去中国参与考古工作吃了闭门羹,张光直也还不死心,1979年中美建交后,他随即提出了中美合作考古的计划,这个计划案在大陆成立不久的社会科学院高层讨论了一个月,此时已升任社科院副院长的夏鼐,依然「主张婉拒」。张光直先是个人投奔不成,继而用中美合作的名义不成,心理一定郁卒。他又想到了一个另辟蹊径的法子,就是走地方路线,直接与大学合作,进行考古研究计划。
在这里,余英时回忆录出现了一个笔误。 《回忆录》说,「一九六0年代他获得四川大学的支持,由川大教授童恩正与他合作,对长江上游进行考古调查。」(页226)实际上,这件事不是发生在一九六0年代,而是在一九八0年代初,张光直自己后来在「哭童恩正先生」的文章中,已有详细记载。张与来哈佛访问的童恩正两人一拍即合。可惜,这件与川大签了合约并获中共教育部批准的合作计划,也被夏鼐搞翻了。地方的大学本不受中央的社会科学院管辖,但夏鼐得知消息后,即电教育部长,运用权势从上面压下来。余英时的推测是,这里牵涉到的可能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立场,是中共官方意志的体现。 (页227)他的推测大致不差。
张光直最初写信给郭沫若和夏鼐表明心迹的1973年和1975年,正是文革期间,毛泽东和四人帮当道。连郭沫若这号学术祭酒的人物,在批林批孔时期,还得首先跳出来自己打脸,更遑论考古所所长夏鼐了。当时学术界人人战战兢兢,有谁敢出头批准一件来自美帝学人的申请呢?用「不置可否」来蒙混过去是最好的办法。如果哈佛学者还不知趣,那就只好「婉拒」了。
然而,这里也还有个人的因素。张光直在悼念童恩正的文章中说,有一次夏鼐来哈佛访问时,很情绪性地告诉他,中国人不能和外国人考古合作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外国人的考古技术发达,中国人很难赶过,如在中国境内一起考古,中国人的成绩一定不如外人。第二、外国人是不能相信的。一个例子是曾留学美国获硕士学位的梁启超次子梁思永,本来和美国学者Herrlee Glessner Creel (顾立雅)说好合写一本书,介绍安阳殷墟。结果,书出来之后(书名The Birth of China,中国之诞生),作者只有Creel。所以夏鼐强调,只要他在考古所任上一日,外国人就不能碰中国的古物。
第一个原因大致近乎事实。民国时期,左翼学者对史语所在傅斯年、李济指导下的考古发掘,批评为重发现,轻研究,资料积累有余,而综合研究不足,在理论方法上十分薄弱。相对与此,左翼自命具有特定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主义,在理论上是优越的。郭沫若根据美国人类学家亨利·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套上马恩理论的条框,写成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被认为是当年主导史语所考古研究的科学主义和自由主义所不能企及的。可是中共建政后,在马列教条的束缚下,考古研究工作并无多少长进。单一、单线、单向性的社会演进观,成为一个紧箍咒。以前对于所谓综合研究和理论方法薄弱的批评,恰恰成为「新中国」考古研究自身的写照。反而是西方的考古人类学不论在技术方法或诠释理论上,都有突飞猛进的成果。大陆考古学门的退化是个事实,但技不如人就要成为故步自封的借口吗?关起门来拒绝与外国合作,又如何提升研究的素质?夏鼐的情绪反应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第二个原因是外国人不可信,合作必定会吃亏。夏鼐耿耿于怀的例子是芝加哥大学的顾立雅,1929年拿到博士学位后不久,申请到哈佛燕京社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研究补助金,到中国参加史语所的考古挖掘,说好要与留美硕士归国的梁思永合作写书,最后书出版(1937)却只有顾立雅一人署名。这件事最初不知是如何约定的。如果属实,违反约定,显然不合学术伦理。梁思永在中共建政后被任命为科学院考古所副所长,与留英归国的夏鼐在考古所有密切的工作关系。因此夏鼐的指控也不能说没有凭据。不过,张光直和童恩正对于同外国学者合作都抱着正面乐观的态度。张光直认为,在二十世纪的今时今日, 全球的考古学家都需自动遵循一套行为准则,而夏鼐抱持的是30年代和40年代的心态。他的民族主义心态,可以理解, 但以之作为拒绝与国际接轨的抉择就是非理性的了。
不幸的是,夏鼐对此始终没有让步。
事实上,随着中国大陆的解冻,华府的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和中共教育部签订了一项在六门学科密切合作的计划。其中唯一的非自然科学的学科就是考古学。这是备受关切的一件大事。据张光直所述,他和童恩正教授一九八二年商定的计划,在中国的部分,是在四川大学设立几个考古实验室:考古学实验室、碳14实验室、考古动物学实验室、考古植物学实验室、地质考古实验室等五个中国当时还没有的实验室。每一个实验室都由一个在那个学科很有地位的学者主持,所有实验室里面所需要的仪器和化学药品,第一年都由美方提供。
计划的另一部分是关于民族植物学与农业起源的问题的研究,由中方童恩正和美方Richard MacNeish教授共同主持。 MacNeish教授是当时世界上研究农业起源的知名学者。两人将沿着四川盆地的边缘去找寻早期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费用由MacNeish通过他的Peabody Foundation(Andover)支付。
可是同一期间在哈佛大学访问的夏鼐,一回北京就驱车到教育部,质问把考古学放在中美合作项目里面的人应受处罚。张、童两人和四川大学商定的交流计划,夏鼐一个字也没看,从原则上就否决了考古合作这档事。童教授回到四川大学,两个人计划的一切都白费了。
笔者看到张光直「哭童恩正先生」的悼文和余英时在回忆录中的叙述,当下的感觉是,作为一个经历许多磨难的学者,夏鼐为何会做得如此决绝?如此不近人情?是为了坚守他大半辈子的民族主义立场?还是另有隐衷?夏鼐回国后不但搞翻合约,还认为应「处罚」当事人,如此反应,所为何来?未免令人难解。
然而,张光直和余英时没有提到的是,就在八十年代初,美中文化交流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

1935年5月傅斯年(左一,前者)、Paul Pelliot (伯希和)(左二)、梁思永(左三)摄于河南西北冈遗址。 (作者提供)
毛思迪闯了祸?
美中建交后,两国于一九七九年年初签署了文化合作协定,以及在文化教育科技等学门的一系列交流计划。史丹福大学人类学系的Steve W。 Mosher (中文名毛思迪)是第一批在文化交流计划下获准到珠江三角洲(广东顺德)蹲点,做田野研究的博士研究生。当时正逢中共开始实行「一胎化」政策。毛思迪亲眼目睹了农村公社进行的一场严厉的运动。中央颁指令,规定广东的人口增长率不得超过百分之一,地方干部就雷厉风行,要求在最短时间内降低怀胎率。毛思迪跟随孕妇到公社卫生院,观察她们像待宰的牲口一样被推上手术台堕胎。逃跑的孕妇,住屋被强制拆毁,有些已达怀孕晚期的妇女,也被迫做危险的堕胎手术。毛思迪将亲眼所见,写成文章,发表在台湾的一本杂志上。不料却引起轩然大波。中共官方愤然要求史丹福大学人类学系开除他的学籍,理由是他去了不该去的地方,见了不该见的场面,收集了不该收集的档资料。更糟的是,他还拍照存证,显然侵犯了当事人的个人隐私,有违学术研究的伦理。毛思迪的同情心无疑是在想生二胎的孕妇和愤怒丈夫的一边。他眼见的农村堕胎结扎实况,令他气愤。但开除他学籍的处分,等于抹杀了几年来他在研究所的努力,他不能不挺身抗辩。事情闹到史丹福大学校长那里,最后仍然维持原议。校长也否认那是受到来自中共的压力。在美国,管理文化交流的委员会,性质上是「非政府组织」,但在中国,却是政府组织。中共恼羞成怒,决定将人类学领域的交流停办三年。
这应该就是夏鼐急忙中止张光直与童恩正商定而他「一个字也没看」的合作计划的真正理由。
夏鼐(下图/作者提供)当时是中央学术机构(社科院)的一个领导人,因此,也许应从「党性」的角度去理解他的立场。

中国大陆在毛死后,随着改革开放,无疑是令当时美国大学的考古和人类学领域的研究院师生响往的一块处女地。想想看,不久前,曾经在印尼做田野研究,蹲点观察斗鸡习俗的文化人类学家Clifford Greertz, 一九七三年出版了《文化的诠释》,挑战Claude Lévi-Strauss(李维史托)等结构功能学派历来所称仪式、制度与文化可透过其所服务的宗旨来理解的观点。对于文化现象,Greertz 强调,该问的问题不是这些现象发挥了什么功能,而是它们的意义是什么。归根究底,人是悬在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网上的动物,而文化就是那些意义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找律则的实验科学,而是寻找意义的诠释科学。对年轻一代的人类学者来说,能在中国这块处女地做田野研究,不正可以在这方面大施拳脚吗?现在偏偏出了个毛思迪来搅和,坏了大家诠释文化意义的美梦,实在太可恶了。这是一种反应。
但也有人认为,毛思迪在中国大陆的农村公社蹲点,他忠实的将他的所见所闻写出来,不畏强权,不受政治绑架,正是追求真相,展现学术自由的榜样。即使他在搜证上有违保护个人隐私的伦理守则,但比起那些为执行中央计划生育政策而把人当做牲口的干部来说,道德上是无愧的。撤销学籍的处分是公允的吗?实情不就是毛思迪把大陆农村见不得人的「脏抹布」抖出来,公诸于世,令他们老羞成怒?
夏鼐一直到1985年去世时,都没有改变他阻止文化交流的立场。借用英国思想史家 Isaiah Berlin(伊赛亚·柏林)所谓民族主义是「压弯的枝桠」的说法,近代中国受到的外在欺凌无疑是沉重的,所以反弹的力道也强大而持久。夏鼐的民族主义,加上他所经历的毛泽东治下新中国的暗黑历史,难免也夹杂了一些「自惭形秽」的成份。
合作之门终于开启
夏鼐去世后,一直要到1992年之后,在考古所王仲殊所长任内,中国大陆的的考古学门才向国际开大门。那也是配合当时邓小平南巡宣布继续改革开放路线。 1994年开始,同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德国、英国、瑞典、法国、俄国、澳大利亚等国的考古研究部门与大学合作,开展大陆的田野考古工作。张光直也就是在这段期间得到中共批准,所以他在1994到1996任职台湾中研院副院长期间想要大展宏图,有一番作为了。可惜如前所述,他在台湾推出的改革方案和设立新的考古研究所的计画都触了礁。但他依然碶而不舍。他的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古代中国考古学)巨著,随着中国大陆的考古发掘新发现而修订多次,从最初的中国文化起源「中原中心论」,发展到最后的「多元起源」的定论。这是他面对发掘研究成果毫不故步自封的态度。
中国大陆的考古人类学研究是有山头主义的。历来有「北派」、「南派」之争,北派偏重于历史文献的研究,南派偏重于考古发掘,其中还涉及学术权力之争,研究资源的分配与论述成见的彼此攻讦。南北两派互相看不起对方。从七十年代初开始的长时期,大陆考古学者苏秉琦对张光直的「中国梦」一直是同情的。在学术上,他也主张同国际接轨交流合作。苏秉琦曾自况他五十知天命,必须「夹着尾巴」做好自己的本职。算算他的年纪,那是在大陆的反右运动后,知识份子都必须「夹着尾巴做人」的时代。据苏秉琦的儿子苏恺之描述,苏秉琦培养的一位学生张忠培,1959年写成的一篇论文初稿,要到二十四年后(1983)才能「贡献给读者」。山头林立,学报编辑人员因门户之见而卡关,是稀松平常相当无奈的事。
苏秉琦对张光直是赞誉有加的。苏恺之记述:
父亲告诉我,张先生自70年代中后期,和大陆有了多次交往,直到70年代末才知道北京大学有考古专业,还有个苏氏。父亲说他是一位很有个性的执着的人,也很难得地在向西方介绍宣传中国考古学,是追求真理而不顾其他世俗观念的人。他的学术成绩和沟通海峡两岸学术关系、培养学生、接待大陆年轻学者访问等作为,都值得赞赏,怪不得李济先生那么喜欢这个弟子。
父亲还说:他起初也信守「中原中心论」,对「多元一统」说不屑一顾,但他凭资料、凭逻辑推理来和你争论,最后在众多的资料面前,终于把他历来固守的观念抛弃了,是位难得的认真做学问的人。
可惜的是, 张光直这个热爱拿铲子挖掘的考古人类学家,经过长时期的折腾,最终圆了他的「中国梦」的时候,他已经患了帕金森症,无法下到坑地实际参与大陆的发掘工作了。有一张照片是在1997年,也就是苏秉琦去世的那一年,张光直拄着拐杖,由两名工作人员搀扶,观察坑地发掘工作。
张光直2001年病逝后,余英时应邀为一本追念文集《四海为家》(北京三联书店2001),作了一篇追悼亡友的文章。
余英时描述,张光直在台湾大学时期就有远大抱负,他毕生追求的治学目标是要根据不断出土的中国考古新资料,重新建构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变迁。随着考古发掘的进展,他也事实求是的不断根据新材料修订他的著作,「每一版几乎都是重新撰写的,他绝不让抽象理论抹杀具体事实。」另一方面,余英时指出,张光直「还有组织与办事的才能,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是一股动力」。所以余在悼文标题中说张光直是「一座没有爆发的火山」。
然而,张光直的抱负,他想要融入中国考古事业的愿望,或许可以说是一种「苦恋」。在他漫长的追求学术交流的过程中,他的「中国梦」却成了他生命中的一场梦魇,最后把他拖垮了。
※作者为前香港《九十年代》专栏作家,着有《最后一个租界:香港变局纪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