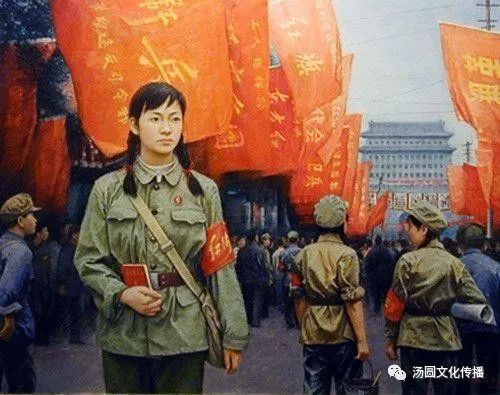当我们走近他们时,有一个像当官模样的人对我们说“你们赶紧回家吧,一会打起来就回不去了。回去有人问你们千万不要说我们在这,记住”!
我和小伙伴们看着他们背着枪,心中着实有些害怕。虽然他们东倒西歪的躺在那里,我们心里对他们还是产生不安和畏惧。于是我们背着筐里的猪菜,还是赶紧连跑带颠的往家里赶。刚到家就听外面枪声响起,枪声来自正南方的杨家坟那边。杨家坟那边地势高,土坟包多,趴在那就能看到中间隔着粮库对面的炮楼。
我家和公社是邻居,中间隔着老王家三间连脊房的院。老王家西院原本是当地有名的地主张财主家,院很大。解放后改成乡公所,也就是后来的人民公社。高大的院墙,南面是能开进汽车的大门洞,北面是走人的宽敞大门。
开始武斗后,兵团造反派在院内东南西北房顶四个角上,修筑了四个炮楼。房下有上房的梯子,房与房之间用松木跳板连接。有事时四个炮楼间不用人到房下,在上面就可以相互联动。
斗批改派用机枪和三八大盖往炮楼这边打枪,杨家坟和公社所在地中间隔着粮库。粮库院墙南离杨家坟有百米左右,枪声两派互相隔空打响。我和家人藏在炕沿下,蹲在地上或躲在窗户垛的两旁,防止子弹进屋伤人。
听到枪声,隔壁的王奶奶急忙迈着走不稳的小脚步从屋内跑到院里,冲着来回在跳板上跑的人喊:“捂住呀,(老太太的大孙子小名叫捂住)你快回家来吧,你再不回来你就把我气死了”。老太太不停的在院里,朝一墙之隔的公社大院里大声哭喊着。
王奶奶那时已八十多岁了,在我的印象中老太太高高的个,全白的头发在脑后梳有一个旮瘩揪。黑色的家织布裤,裤腿口用黑布带绑着,上穿深蓝色旁开口大襟家织布上衣。老太太嗓门大,她来回迈着三寸金莲的脚步,随来回在跳板上跑的人南北急走着,拍着大腿声嘶力竭地大声嚷。
因为兵团造反派里有她独苗大孙子,她不惧怕外面的打枪声,她唯一惧怕的是对面不长眼的子弹打在孙子身上。枪子不长眼,子弹不留情。老人家的呼喊是为了赶紧让孙子回家,别让枪子碰到孙子,孙子不回音是为了自己追求的理想信念,两代人各有各的心思和目的。
一直到日落黄昏,枪声不响了,斗批改造反派撤退了。这时公社兵团造反派队伍里有一个人也开始忙活起来,他天黑前和太阳出来前,他都有自己特殊任务。据说他是邻村一个光棍,无父无母一个人。人称杀狗的,在没参加造反之前靠杀狗卖烀狗肉维持生计。参加兵团造反后他的职责就是,在天黑前埋设地雷,防止斗批改造反派晚上来端炮楼。埋设区域就是公社大院的四周,包括左邻右舍的树下。院墙外,茅房旁。用铁线围上,下面把地雷串联起来。也不知道是不是真有地雷,早上再由他全部撤掉,反正吓得大家一到晚上都不敢出门,就是上厕所都的小心翼翼。
直到有一天斗批改造反派有一百多人的队伍,穿着不太整齐的衣服浩浩荡荡从大街上大摇大摆走过,是不是有意来,在兵团造反派眼皮底下来示威就不得而知了。反正兵团造反派大门紧闭,也没有人敢开门。据说人都去外地支援同伙了,后来得知,这时的护院人数只有十几个人。
几天后,部队开着解放牌汽车,来到公社收缴武器。车上的军人全副武装,驾驶楼上有机枪。机枪旁有正副机枪手和子弹木箱,子弹成排连着子弹箱上膛。把收缴的武器全部装在汽车上拉走,这场两派对立才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