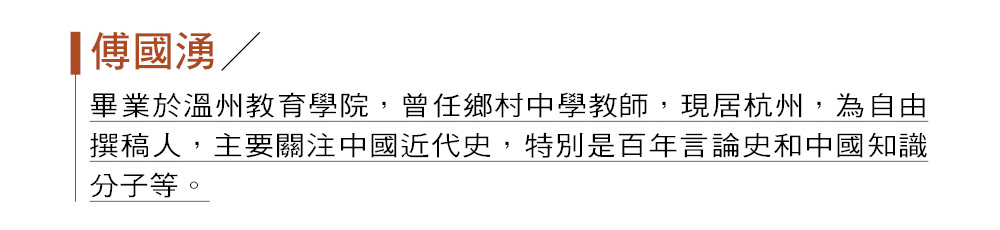作者:傅国涌 来源:上报 2024年02月03日

施明德自称「奉献者」,名副其实。与其他「美丽岛」的受难人和辩护者不同,他最后没有成为掌权者,终其一生都是反对者。 (图片取自施明德脸书)
一、「奉献者」
2024年1月15日早上,我听说施明德离世的消息时,正好在读旧书店淘来的一本旧书。那是1988年初版的《施明德的政治遗嘱——美丽岛事件军法大审答辩全文》,薄薄的小册子,仅有142个页码,还有他微笑着被押上法庭的照片。所谓「政治遗嘱」是他1980年3月26日在景美看守所含泪写下、提交给警备司令部军事法庭的长篇辩词。两个半月前,在经过传奇的逃亡生涯之后,他第二次被捕入狱。
在此之前,1962年6月16日到1977年6月16日,他已作为政治犯在狱中熬过了十五个年头。所以他才会在辩词中说:「我,和大家一样,也有七情六欲。我却必须压抑欲望而不变态,忍受千辛万苦而不心存怨怼,像苦行僧般的在牢狱中接受十五年——不是十五天或十五个月——形形色色的折磨、锻炼。只是我比苦行僧更苦。苦行僧是出世的,我却是入世的。以入世的心境度出世的生涯,其艰其苦其难又岂是我的话语所能形容或传达的?」
1962年入狱时,他只有21岁。那一次他以「叛乱罪」被判无期徒刑,直到1975年因为蒋介石去世而获减刑,服刑十五年,刑讯中牙齿全部脱落。
1980年1月8日,他以「叛乱罪嫌」脱逃时,孤岛南北的电线杆子上到处都是悬赏他的通缉令,赏金从50万元新台币提高到100万元新台币。站在军事法庭上,他骄傲地宣读这篇辩词,最后有这样一些话:
我很清楚,非常清楚,如果我不放弃我的信念,便只好走进国民党的刑场或老死「古拉格群岛」中。
我又来了。以坦然含笑的姿态,站在诸位的面前了。我早已做了抉择。
每个时代都有奉献者。奉献者总是扮演着悲剧的角色。奉献者深知自己的旅程必是孤单、坎坷、凄惨和布满血泪的。奉献者总是不为他的时代所接受,反遭排斥、欺凌、羞辱、监禁和杀戮。但是,奉献者所爬过的羊肠小径,必会被后继者踩成康庄大道。奉献者的肉体也会腐朽,但是他的道德勇气和择善固执的奉献精神,必会增益人类文明,与世长存。奉献者不属于今天,但是他会活在明天!
最后,我要重申奉献者的一项共同信条,来结束我今天,也许也是我此生的「最后陈述」——我并不奢望在这个世俗的「法庭」中求得一项公正的判决,但是我毫不怀疑地深信:总有一天,历史法庭一定会还我公道!
仅仅服刑十年,他就等到了这一天。 1990年5月11日,年近半百的他无罪出狱。不到四年前,他的同案和辩护律师们已冲破党禁,蒋经国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默认了这一事实。但在1997年4月1日到5月11日,他还坐过一个多月的牢。
我之所以称他为坐牢家,就是他三次入狱,在狱中几乎消耗了二十五年半的生命。他至少两次与死刑擦肩而过。 1980年的军法大审,视死如归,用在他身上是贴切的,当年还不到四十岁的他曾几次在法庭上呼喊:「请判我死刑。」根据动员戡乱时期惩治叛乱条例,他也确实会判死刑,但因为蒋经国交代的底线:「不管你们怎样处理,我不希望看到有死刑。」他才再次获刑无期,其他七个同样以军法审判的同案,分别获刑二十年、十二年。十年前,我曾写过《蒋经国处理「美丽岛事件」的决策过程》一文,首发于《炎黄春秋》2014年6月号。
二、坐牢家
他离世第二天,有位律师在《联合报》发表悼念文章,引用了法国诗人布德赖尔的一句诗:「他是沉沉落日,这颗恒星,坠落时,美不胜收,但失去了热烈,只有满满的哀愁。」落日,哀愁,以布德赖尔的诗来纪念他对人世的告别是恰当的。
他自称「奉献者」,名副其实。与其他「美丽岛」的受难人和辩护者不同,他最后没有成为掌权者,终其一生都是反对者。
作为一个浪漫主义的反对者、受难者,他参与推动并创造了历史。
八十三岁不过是他的肉身。他的生日与死日恰好在同一天。
而作为一个人,绝不只是肉身的存在。他的一生可以歌,可以哭,几次搅动全岛,激起了时代的浪花。
1979年12月,他作为「世界人权日纪念大会」总指挥,在全岛上下遭到无死角的追捕,成为家喻户晓的「江洋大盗」,牵连无数人锒铛入狱。
1980年7月,他再次被押送到曾经让多少母亲长夜哭泣的火烧岛。他说这是孤悬在太平洋上的一个神秘而寂寞的小岛,有被火燃烧似的土壤,被火燃烧似的命运。
在他离世次日,《中国时报》刊出对陈文茜的采访,她曾听他本人回忆,「当年被关在绿岛,前妻已经离开,家人并不知道施的家变,他身无分文,把内衣撕成一块又一块的布,每天上午的白饭,只吃半碗,另一半做成米浆,洗净布料,重复使用,因为当时连一张卫生纸都买不起。」
他的前妻爱琳达是美国人,斯坦福大学人类学博士候选人,在他两次监狱的缝隙里,他们相识并结婚,婚宴上,《自由中国》创办人、1960年被判刑十年的前辈雷震也到场祝贺。爱琳达一直记得1979年12月10日晚上十点半,在美丽岛高雄服务处的转角处,他们的四周摇曳着火把的光芒,弥漫着催泪瓦斯的爆炸声和浓雾,他说了当夜最后一句话:「如果我必须因此在狱中了此残生——而人民能坚定地站起来反抗压迫者,并且,令人瘫痪的恐惧感能从此结束——我甘愿!」
2015年10月初,我和妻子从台东坐船到绿岛,在海边的花岗石上密密麻麻的名字中,我找到了他的名字。在他昔日的囚室前,我曾伫立沉思良久。当时,我并不知道他在绿岛经历的不堪。那次在旧书店淘来的旧书《囚室之春》,是1989年12月为他被囚二十五年而编的,离他第二次出狱还有半年。火烧岛上不生长水果,蔬菜也满足不了岛上的需要,何况囚犯。他们多次自己买来绿豆,动手孵绿豆芽,他认真观察、记录、分析,还写了一篇《孵豆芽的启示》。那是1975年9月30日,当时,他已被囚禁了十三年,并不知道两年后就能走出火烧岛。
这个火烧岛也就是《绿岛小夜曲》中的绿岛。小时候,我听这首歌只觉得好听,却不知道背后的无比伤痛。
他不仅是坐牢家,也是绝食家,几乎创造了人类奇迹。他曾在狱中绝食4年7个月,强插鼻胃管灌食3040次。因为绝食,他被送进三军总医院特别隔离区,《囚室之春》就是在这里写的,他说自己在被囚禁的病房里养过枫树、榕树、铁树、橡树、万年青等绿植,因为缺少阳光都要枯萎了,只能将「小植物园」从病房移到见得到阳光的走廊上。此前,他曾日复一日,看着断崖绝壁上的榕树,阳光不足,没有肥沃的土壤,沐浴海风、海雾,还能顽强地生长。毕竟绿岛的断崖上还有阳光。
如有机会,将来我还想再次去绿岛看看他们受难的地方,听听大海不灭的涛声,重温他在绿岛写下的文字:「更深人眠,从囚窗眺望天宇,听海涛拍击礁石,细细缅怀台湾四百年来的悲哀史实,细细咀嚼自己十余年中血泪凝聚的遭遇,我突然不再沮丧,不再痛苦。顷刻间,我为台湾人民、为我个人及和我同样命运的人们感到骄傲和喜悦!并充满自信!」
三、落日的哀愁
在威权统治之下,他是浪漫的反抗英雄,成为不可摧毁的反对象征。在政治转型之后,他又毅然退出自己参与创立、担任过党魁的政党,甚至再次披挂上阵,发起百万人倒扁运动。红衫军运动是他第二次自任总指挥。
当他离世时,陈水扁公开悼念,称他为一代枭雄、民主先知,并说「先知都是寂寞的」。
这一次,他不需要付出牢狱的代价,但也逃不出被边缘化的命运。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他将渐渐隐入历史深处。
如今,他终于走了。
对于他的赞美铺天盖地,台北地标101点灯向他致敬——「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一生奉献台湾」……这些也都没有错,却遮不住他的短处,比如他的身上浓厚的民粹色彩,对文明大势、国际问题的隔膜和误判。 2023年10月13日,他的生命已进入倒计时,最后一次公开发表言论:「我是巴勒斯坦人,我哭泣。」竟然将哈马斯与巴勒斯坦问题混为一谈,可惜了。当天,记者接到他的电话,没讲几句,就听到他在电话的那一头哭了出来。一代反对强权、不畏死亡的浪漫英雄,毕竟勇气有余,见识不足。我们仰望他蔑视死刑、笑傲死亡的大勇,依然不能回避他致命的缺陷。是者是之,非者非之。这才是面对历史人物应有的态度。
尽管如此,在需要舍身的反抗时代其英雄人格依然值得高度肯定,他对孤岛政治转型的贡献更应大书特书。我只是为他感到悲哀,那是落日的哀愁。一代人过去了,正如一位元记者说的,他的逝去真正代表了那个时代重要篇章的终结。无论怎样的惊心动魄,最终都要归于平淡,他在蒋介石、严家淦、蒋经国、李登辉时代都坐过牢。 1989年8月22日他在三军总医院写下的散文《囚室之春》最后说到,自己二十几年都在坐牢,一直要求自己做一个「够格的政治对手」或「可敬的敌人」。他不断地鼓励自己:「你不属于今天,但一定会活在明天!」
2006年8月,他已65岁,还发起反对陈水扁贪腐的「倒扁运动」。什么时候,他都可以说不,敢于说不。他相信,「民主这一课没有句点,必须一代接一代努力下去。」《中国时报》要闻版的标题中说他:「从冲撞国民党政权到撼动民进党政权」。上个世纪70年代末,正是第一次出狱不久的他率先提出将《美丽岛》政团作为一个「没有党名的党」。也正是导致他第二次入狱的「美丽岛案」撬动了国民党在岛上的一党统治。他的历史作用无人能够替代。
在生命的终点即将到来前,他对家人说:「不要告别式、也不要追思会,我一辈子都在搅动台湾,这次就让我安安静静地走吧」。喜欢轰轰烈烈的一代反抗英雄,最后要安安静静地离开这个世界。 2024年1月16日,《中国时报》头版刊登记者曾薏苹、崔慈悌的报导,他的两个女儿施笳、施蜜娜说:「我们的父亲没有忌日,只有生日。」1月15日清晨,当他停止呼吸,亲友们仍为他唱生日歌、切蛋糕,病房里弥漫着香水百合、玉兰花的气味,正是他生前所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