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2024 年 4 月 25 日来源:思想坦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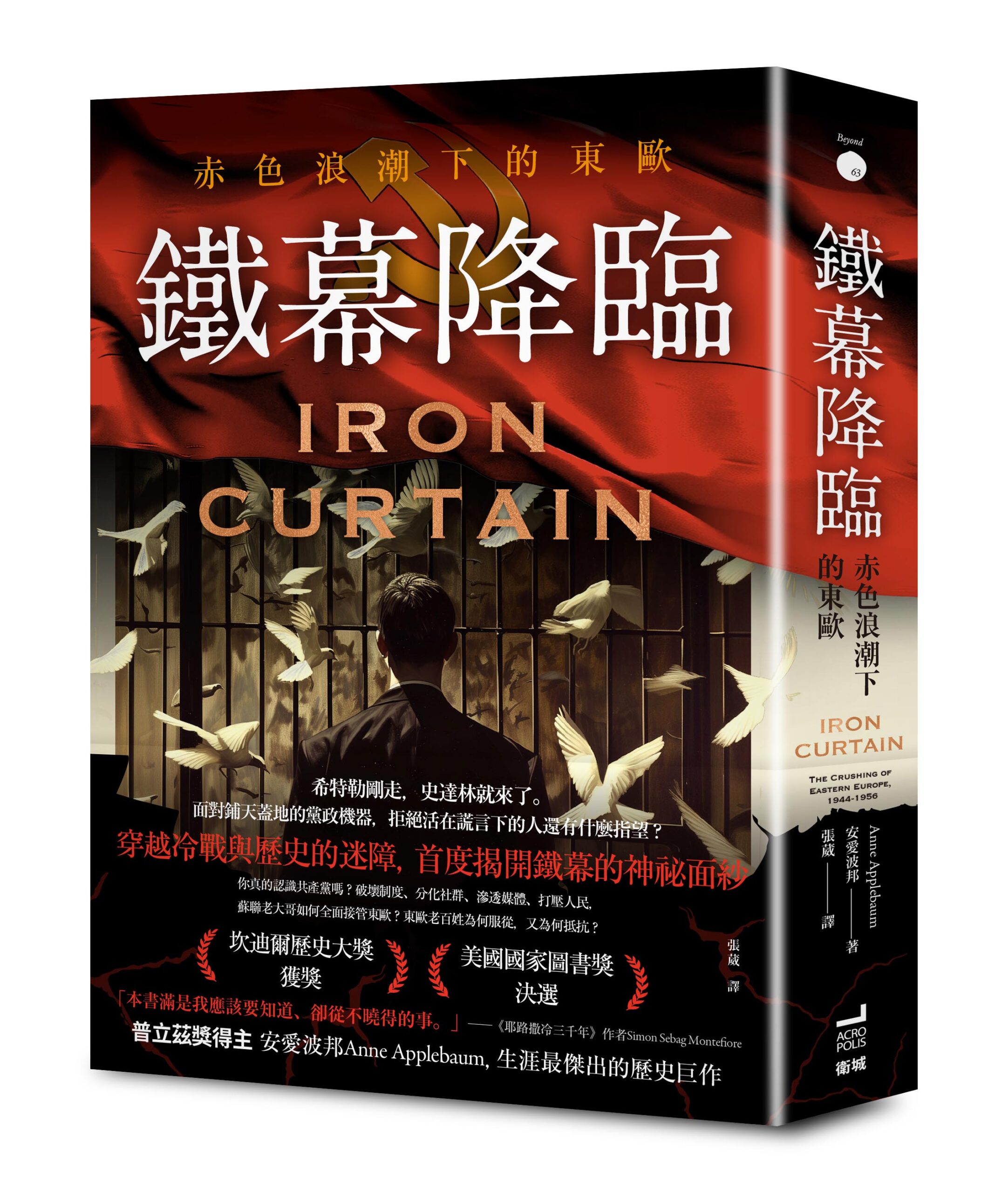
第一章:零时降临
「凌乱不堪的废墟,纠结缠绕的电线,扭曲的尸体,死掉的马匹,遭轰炸而倾覆的桥梁碎块,从马脚上扯下来的血淋淋马蹄,损坏的枪枝,散落的弹药,夜壶,生锈的洗脸盆,漂浮在带血泥泞中的稻草碎片和马内脏,相机,面目全非的汽车,战车的碎片。这些事物见证了一座城市所蒙受的恐怖苦难……」──洛松奇(Tamás Lossonczy),一九四五年于布达佩斯
「伟大的首都被摧残至面目全非;昔日强大的国家如今不复存在;原先的征服者曾如此残忍傲慢,曾如此盲目坚信自身使命是主宰其他族类……而今他们在废墟中翻拣着,这群破碎而茫然、发抖而饥饿的人类失去意志、没有目标、没有方向。如何才能找到忠实精确的语言来描述此番场景?」──夏伊勒(William Shirer),一九四五年于柏林
「我觉得自己似乎行走于尸体之上,随时都会一脚踩进血泊里。」──雅妮娜(Janina Godycka-Cwirko),一九四五年于华沙
爆炸声回荡在夜里,白日也总能听到炮声隆隆。落下的炸弹、机枪的轧轧声、向前滚压的战车、轰隆隆的引擎、着火的建筑都发出声响,声音笼罩整个东欧,预示着红军来临。随着前线逼近,地面震动着,墙也在颤抖,孩子们发出尖叫。然后,一切戛然而止。
无论在何时何地,战争结束都会带来一种突如其来的诡异寂静。 「夜里太静了,」有位不具名者如此记载着战争结束时的柏林。
她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早晨走出家门,外面半个人也没有。 「目光所及处没有任何平民,俄国人完全掌控了街道。但每栋房子里都有人在窃窃私语或瑟瑟发抖。谁想像得到会有这样一个世界隐藏在这里,如此惊恐,就在这座大城市中央?」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二日上午,围城结束那天,有位匈牙利公务员在布达佩斯街上也遇见了相同的寂静。 「我到了城堡区,四顾无人。沿着威柏奇街走,沿路只见尸体和废墟、手推车和马拉板车⋯⋯我抵达圣三一广场,决定进议会瞧瞧,说不定有人在里面。但里头空无一人,所有东西都被掀翻了,就是半个人影也没有。」
就连华沙这座早在战争结束前就遭摧毁的城市(纳粹占领军在秋天那场起义后将华沙夷为平地),也在德军全面撤退的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六日那天变得更加安静。华迪洛.史匹曼(Władysław Szpilman)是仍躲在华沙废墟中的极少数人之一,他听见了这个变化。史匹曼在回忆录《战地琴人》(The Pianist)中写道:「即便是华沙这个在三个月前已成死城的地方,也从未见识过这样的死寂。甚至听不见外头守卫的脚步声,我搞不懂发生了什么事。」翌晨,「巨大而嘹亮的声音打破寂静,这是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声音。」红军来了,用波兰语广播着华沙已被解放的消息。
这就是人们有时称之为「零时」(Stunde Null)的一刻:战争结束、德军撤退、苏联进驻,这是停止战斗、重新开始生活的时刻。大多数关于共产党接管东欧的历史正是由此刻开始书写,而这也很合理。
对于那些经历了此番权力更迭的人来说,零时感觉起来像是转折点:具体而有形之事结束了,全新而未见之事开始了。许多人对自己说,从现在开始,一切都会不同。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不过,以战争终结作为起点来书写共产党接管东欧的历史虽然合理,但就某些方面而言也相当误导他人。毕竟,这个地区的人民在一九四四年或一九四五年时面对的可不是一张空白画布,而他们自己也不是从零开始。他们不是从某个地方冒出来,没经历过任何事且准备好过新生活的一群人。正好相反,东欧人是从自身家园的断壁残垣中爬出来,从游击队藏身的森林里走出来,从监禁他们的劳改营中溜出来,踏上漫长困难的返乡之旅(如果他们的身体状况还能负担)。有些东欧人在德国投降时甚至仍未停止战斗。
东欧人爬出废墟时,看到的并不是全新的处女地,而是满目疮痍。捷克作家柯瓦莉(Heda Kovály)在回忆录中写道:「战争结束就像是驶向隧道的尽头。」你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前头的光,那道持续而稳定的光。你到达彼端的时间愈长,那光芒对于蜷缩在黑暗中的你而言就愈发耀眼。但当你乘坐的火车终于冲出隧道口、进入灿烂的阳光下,眼前所见却是一片荒芜,满布杂草、石头及垃圾堆。
当时拍摄于东欧各地的照片中,尽是启示录般的场景。被夷为平地的城市,绵延数亩的瓦砾,遭到焚毁的村庄,曾是房屋但如今已焦黑冒烟的废墟。纠结的铁丝网,集中营、劳改营、战俘营的遗址。荒芜的田野,战车碾压的痕迹,毫无农业、畜牧业或任何生活的迹象。在刚被击溃的城市里,空气中总弥漫着尸体的味道。有位德国战后幸存者写道:「我读到的叙述总是以『带着甜味』来形容,但这模糊到完全不足以描述那股刺鼻怪味。与其说是种气味,不如说是某种聚集在你脸孔前方的浓稠气体,坚实厚重且带霉,令你无法呼吸。你只能后退,像是有人出拳打你。」
乱葬岗随处可见,人们小心翼翼穿越街道,仿佛走在墓园。在适当的时刻,人们开始挖掘,将尸体从庭院和公园移到集体墓地。时常有葬礼和重新安葬的仪式举行,不过华沙却有场著名的葬礼遭中断事件。一九四五年夏天,一列送葬队伍正缓慢穿越华沙,但身穿黑衣的送葬者看到了不寻常的景象:一列行驶中的红色华沙轻轨电车。人行道上,行人停下脚步,许多人跟着电车跑了起来,大声鼓掌欢呼。不寻常的是,送葬队伍跟着停下脚步,正为死者哀悼的送葬者也受到身旁气氛感染,他们转向电车,开始一起鼓掌。
这种情况并不罕见,生还者有时会陷入一种奇异的欢快感之中。能活下来令人如释重负,悲伤与喜悦交杂,而贸易往来与重建工作转瞬便自动开始。一九四五年夏天的华沙热闹有如蜂巢,作家基谢莱斯基(Stefan Kisielewski)如此写道:「在废墟般的街道,前所未见的骚动涌现。蓬勃发展的商业,忙进忙出的人们,随处可闻的谈笑声,谁能想到这群人是巨大灾祸的受害者,是几乎没能从灾难中生还的人,他们如今仍生活在严苛而不人道的环境中……」桑多.马芮(Sándor Márai)在同时期的一部小说中如此描述布达佩斯:
无论这座城市或这个社会还剩下什么,所剩之物都凭着一股热情、愤怒、纯粹的意志力而萌发着生机,挟着强大的力道,态度坚毅,身段灵活。看起来似乎什么都没发生过⋯⋯大街上,通道旁冒出摊贩,兜售各式美食与高档商品:衣服、鞋子,什么都有,甚至可见法国金币、吗啡和猪油。生还的犹太人从涂着黄色星号的房子内踉跄走出,一两个星期后,他们便开始在买卖中杀价,他们身旁甚至还躺着人和马的死尸⋯⋯瓦砾堆中,人们为了英国布料、法国香水、荷兰的白兰地和瑞士的手表讨价还价……
这种对于工作与重建的热情将会持续多年。英国社会学家亚瑟.马威克(Arthur Marwick)曾推测,可能是国家失败的经验带给了西德人重建的动力,他们想找回民族自豪感。他认为,德国所经历的大规模崩溃可能促进了战后的繁荣发展:在经济灾难与个人生活的灾难之后,德国人欣然投入了重建行动。但德国(东西德皆然)并不是唯一一个渴望复原与「重回正轨」的国家。在回忆录与回顾战后时期的谈话里,波兰人和匈牙利人也都反覆提及自己是多么迫切地重回学校,拾起工作,追求没有暴力干扰的生活。而共产党已准备好利用人们对于和平的渴望。
无论如何,财产损失都比东欧的人口损失更容易复原。东欧所承受的暴力规模远大于西方所能想像。二战期间,东欧经历了史达林和希特勒意识形态中最疯狂的部分。到了一九四五年,西起波兹南(Poznań)、东至斯摩棱斯克之间的这片土地,大多曾落入各方占领军之手不只一两次,有些地区甚至高达三次之多。一九三九年签订《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之后,希特勒便由西方入侵此地,占领波兰西半部。史达林则由东方进犯,占领波兰东半部、波罗的海三国与原属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地区。一九四一年,换希特勒由西边占领前述地区。一九四三年,局势再度生变,红军从东面进军,这片土地又一次易主。
也就是说,到了一九四五年,已有两个极权国家的致命大军与凶恶秘密警察在这块土地上来回逡巡,在东欧的民族与政治层面留下深远的影响。举例而言,勒沃夫(Lwów)曾两度落入苏联红军之手,一度落入德国国防军之手。战后,这座城市的名称变成了勒维夫(L’viv),此地也不再位于波兰东部,而是位于隶属苏联的乌克兰境内。战前定居于此的波兰人和犹太人不是遭到谋杀,就是遭遣送出境,取而代之的是由附近乡村移入的乌克兰裔居民。
放眼全欧洲,出于政治动机的杀戮行动大多发生在东欧、乌克兰与波罗的海国家。提摩希.史奈德在《血色大地》中如此写道:「希特勒和史达林虽分别崛起于柏林与莫斯科,但两人实现改革大业的地点主要是位于这两者之间的区域。」对于任一东欧民族拥有国家主权这样的概念,史达林和希特勒嗤之以鼻,他们致力于消灭东欧菁英。德国人认为斯拉夫人是低等人类,地位不比犹太人高多少。在萨克森豪森与娘子谷(Babi Yar)之间的大地上,他们毫不犹豫便下令在街头任意杀戮、执行大规模公开处决,仅为了替一名死去的纳粹士兵复仇便烧毁整个村庄。与此同时,苏联则认为东欧诸邻是资本主义与反苏根据地,其存在是对于苏联的挑战。一九三九年、一九四四年与一九四五年,红军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这块新占土地上逮捕的不只是纳粹或与纳粹通敌者,他们也逮捕所有理论上可能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人:社民党人、反法西斯分子、商人、银行家、批发商—与纳粹所针对的族群大幅重叠。虽然西欧也有平民死伤,英军与美军也有偷窃、品行不端或暴虐事件,但大多数情况下,英美军队的目标是消灭纳粹,而非消灭被解放国家内部的潜在领导阶层。他们大都也对各地反抗军领袖尊重以待,而非饱含疑虑。
东欧也是纳粹尽情施行大屠杀之处,多数的犹太隔离区、集中营和屠杀处决地都位于东欧。史奈德指出,希特勒于一九三三年上台时,犹太人占德国人口不到百分之一,其中有许多人设法逃亡。希特勒希望打造一个「没有犹太人」的欧洲,若要实现此愿景,德国国防军就必须征服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最终直抵匈牙利和巴尔干地区—因为欧洲大多数的犹太人都以此地为家。死于大屠杀的五百四十万名犹太人大部分都住在东欧,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大多也被遣送至东欧杀害。纳粹对于东欧人的鄙视与他们决定以东欧为犹太人处刑场一事密切相关。低等人类的土地,适合执行低等残忍的行动。
最重要的是,东欧是纳粹主义与苏维埃共产主义交会碰撞之处。虽然两方在战争初始时是盟友,但希特勒一直都想对苏联发动毁灭性战争;而在希特勒进犯后,史达林也誓言要还以颜色。所以比起西欧,红军和德国国防军之间在东欧的战斗要来得更加激烈血腥。德军相当害怕所谓的「布尔什维克蛮军」,他们曾听闻过许多关于这群人的恐怖传说;二战打到最后,他们更是不顾一切地和红军拼命。德军特别看不起东欧平民,对当地文化和建设毫无尊重可言。某位德军将领确实出于对巴黎的柔情与尊重而违抗希特勒的命令,保全了巴黎,但其他德国将领则毫不犹豫地将华沙夷为平地,同时摧毁大半个布达佩斯。西方空军并不在意东欧的古建筑,盟军轰炸机也在此地杀戮破坏:不只轰炸柏林和德勒斯登,也轰炸了但泽和柯尼斯堡(即今日的格但斯克和加里宁格勒)等其他许多地方。
随着东线战场延烧至德国本土,战争也愈趋激烈。红军像是著了魔似的不断向柏林推进。苏联士兵自战争初期便习惯在告别时高呼:「柏林见!」史达林拼了命想在「其他盟国」抵达柏林前抢先攻下此地,他麾下将领明白这点,美军也心知肚明。艾森豪将军知道柏林的德军宁死不屈,他不愿美军平白丧命,决定把柏林留给史达林。邱吉尔则反对这么做:「如果俄国人拿下柏林,他们会认为自己对盟国共享的这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让这种想法留在他们脑中不会不太恰当吗?此事在他们心中催生出来的氛围,难道不会导致未来出现重大问题吗?」但艾森豪的谨慎获得了最终胜利,英美联军缓慢向东推进—美国的马歇尔将军(George C. Marshall)曾表示他「不愿为了纯粹的政治目的而令美军身陷险境」,而英国陆军元帅艾伦.布鲁克(Alan Brooke)爵士也认为「向德国内部推进的距离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吻合我们的最终边界」。与此同时,红军则直直开向德国首都,所经之处寸草不生。
从统计数字便可得知事态有多严重。英国有三十六万人死于二战,法国有五十九万人死于二战──这样的伤亡数字相当可怕,但仍不到两国人口的百分之一点五。相较之下,波兰国家记忆研究院则推估波兰大约有五百五十万人死于二战,其中约三百万是犹太人。也就是说,波兰失去了约百分之二十的人口,每五个波兰人就有一个没能活下来。即便在战争不那么惨烈的东欧国家,死亡人口的比例也比西欧国家还高。南斯拉夫死了一百五十万人,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匈牙利的死亡人数是总人口的百分之六点二,捷克的死亡人数则是战前总人口的百分之三点七。至于德国本土,死亡人数介于六百万至九百万之间(差异取决于「德国人」的定义为何,因当时的德国国界常有变化),大约是德国总人口数的十分之一。在一九四五年的东欧,几乎找不到哪个没受重创的家庭。
战后的尘埃逐渐落定,我们开始看见许多人即便生还也早已远离家园。许多东欧国家在一九四五年的人口统计、人口分布与民族构成,已与一九三八年大不相同。纳粹占领东欧后有好几波遣送和重新安置的行动,导致东欧人口分布出现剧烈变化,其影响之重大,西欧人至今未能充分理解。德国的「外来居民」被迁入德占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目的是为了改变特定地区的族群分布,至于该地原本的居民则遭驱赶或谋杀。早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住在罗兹较好区域的波兰人和犹太人就被赶出家园,好让德国官员进驻。之后的几年,纳粹将二十万左右的波兰人从罗兹遣送到德国,强迫他们在该地劳动。犹太人则被赶到罗兹的犹太隔离区,大多数人都死在里头。德占政权把这些人的房子分配给德国人,包括来自波罗的海和罗马尼亚的德裔民众,有些人还以为自己分到的是遭人遗弃或无人关照的房屋。
战后,人们开始将事情恢复原状或遂行报复。一九四五、一九四六与一九四七年是难民流徙之年。德国人向西迁移,德国劳改营和集中营内的波兰人和捷克人返回在东方的故乡,被遣送至苏联的人回来了,战场上的军人也开始返家,流亡者纷纷从英国、法国或摩洛哥返国。但许多难民回到家乡后,却发现家乡已经面目全非,只得移居他处。杨.格罗斯估计,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三年间,约有三千万名欧洲人遭到驱赶、重新安置或遣送他处。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八年间,又有两千万欧洲人移居别地。克丽丝蒂娜.克斯顿指出,一九三九至一九五○年间,每四个波兰人就有一个不住在战前的家。
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一无所有地返回家园,不得不向其他人(教会、慈善机构或国家)寻求帮助,无论是什么样的帮助。许多在战前不需仰赖他人的家庭,如今却得在政府单位门前排队,等着政府分配房屋或公寓。曾凭双手工作挣得薪水的人,如今却必须从别人手中求得物资配给卡,或是一份政府机关的工作。被强行赶出自家门口的难民,心情自然不同于为了赚钱而移居他方的移民,前者的处境带来了他们以前也许从未经历过的依赖感与无助感。
更糟的是,东欧不仅是地貌受到严重摧残,经济上也承受了惨痛破坏,其规模之庞大同样令人难以理解。并非每个东欧国家在战前都很富裕,但此地原本在一九三九年时并不像一九四五年时那样远远落后于西欧国家。确实有些东欧人从战时的枪枝、战车生产需求中获利(许多经济史家讨论了当时产业工人阶级的成长,在波西米亚与摩拉维亚地区尤甚),但二战的下半场对所有东欧人来说都是场大灾难。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六年,匈牙利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一九三九年的一半。统计指出,在二战最后几个月里,匈牙利有四成的经济基础建设被毁,首都布达佩斯更有四分之三的建筑遭到破坏,其中百分之四被夷为平地、百分之二十二变得无法居住。该国人口只剩战前的三分之二。德军在撤离此地时,带走了该国大部分的铁路车辆,剩下的车辆则被后来的红军以赔偿为名征收。
至于波兰,一般估计其经济损失亦在四成左右,但有些地区承受的损失甚至更高。波兰的交通基础建设被破坏的程度格外严重:全国有一半以上的桥梁被毁,港口、航运设施和四成铁路设备也面目全非。多数的大城市遭到严重破坏,也就是说有许多房舍、古代建筑遗迹、艺术品、大学和校园都永远消失。华沙市中心有高达九成的建筑受到部分或全面性的破坏,因为德国人在撤退时对此地进行了系统性轰炸。
其他德占城市也一样凄惨,这得归责于盟军那些引发大火的空中轰炸,也得怪罪希特勒命令德军在巷战中坚持到最后一兵一卒。即便是在破坏范围没那么广泛、也没遭到广泛轰炸的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人民的损失同样惨重。举例而言,罗马尼亚失去了他们的油田:那是原本在一九三八年之前,罗马尼亚三分之一国民总收入的来源。
战争还以其他难以量化的方式影响了东欧经济。杨.格罗斯和布莱利.亚柏兰在两篇颇负盛名且实至名归的文章中探讨了二战造成的社会后果,文中指出东欧大部分地区(当然包括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及德国本土),大规模征收私人财产的其实是二战期间的纳粹与法西斯政权,而不是战后的共产政权。在中欧地区,当地政权和德占政权大规模征收了犹太人的财产与企业,占领后期则进行了更广泛的德国化行动。这类事情有时在暗中进行,例如在捷克,德国的银行控制了捷克的银行,因此常由德国银行来裁定捷克某银行或企业是否有还款能力──当捷克银行或企业无力还款时,就由德国银行或企业出手相救,从而取得控制权。这类情事有时也明目张胆地进行,例如在波兰,许多工厂和企业虽然名义上仍属波兰人,却常被安插德国籍的经理或董事。
占领期间,地区经济的方向也遭到改变。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五年间,东欧各国对德国的出口额增加了两至三倍,而德国对于当地产业的投资亦然。从一九三○年代初起,德国经济学家便不断主张在东欧建立经济殖民地,而德国企业在占领期间确实也据此进行:通常是透过私占犹太人的工厂与企业,有时甚至也私占非犹太人的企业。整个地区成了自给自足的封闭市场,这在过去也是前所未见。这代表当德国崩盘时,该地区的国际贸易关系也会随之崩溃,最终导致苏联轻易取代德国的地位。
出于同样原因,德国战败也导致了一场所有权风暴。战争结束时,德国的企业家、经理和投资者不是逃离当地就是被杀害,许多工厂遭弃置、失去主人。这些工厂有的被工厂委员会接管,有的则由地方当局接手。遭到遗弃的产业最后大半都收归国有—如果厂内财产没被整套打包运到苏联的话。苏联认为所有「原属于德国」的东西都是对于战争的正当赔偿,而对此表示抗议的人是出奇地少。一九四五年时,政府当局已经可以直接没收私人财产而不提供任何补偿,这成了东欧的既定原则。所以当政府开始将一切大规模收归国有时,也没有人真的感到讶异。
作者为美国著名媒体人、历史学家暨公共知识分子,普立兹奖得主,《大西洋月刊》与《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共产政权在东欧倒台时她正以《经济学人》外派记者身分派驻波兰,是第一批带回当地消息的记者。安爱波邦同时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负责研究政治宣传与不实资讯。着有《古拉格的历史》、《红色饥荒》、《民主的曙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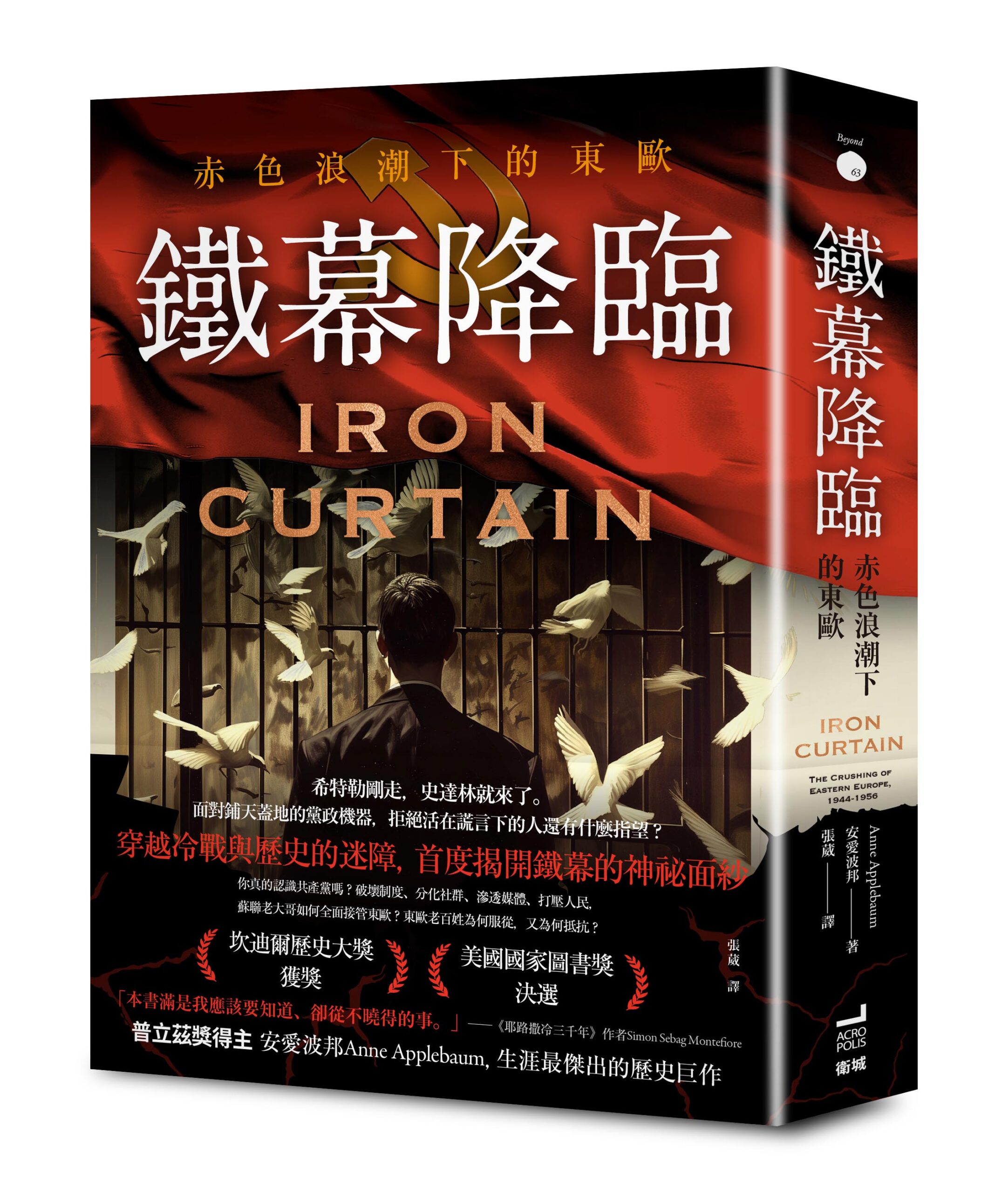
书名:《铁幕降临:赤色浪潮下的东欧》
作者:安爱波邦(Anne Applebaum)
出版社:卫城
出版时间:2024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