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白立丁(书评人) 转自新世纪
当下的环境对于历史和思想研究者造成了诸多的困境和挑战,其中之一就是我们能否为诸如「文革」、「民主运动思潮」、「九十年代争鸣」、「当代思想史」沿着官方还是「非官方」所掌握的历史材料进行尝试需求一种「客观性」的叙述和价值的判断;还是应当如同「盲人摸象」般,在有限可用的材料中寻找某种关联和诠释取代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
在文革和后文革的思想史探究中,这种问题就更显得突出。尽管在「文革」研究和后文革时代研究已经有了相对深入的研究和争论,但是在公共领域的主导性叙述(如「支持」和「否定」文革或改革开放此类的价值判断)已经成为主流甚至这种「辉格党式的历史阐述」倒过来影响着研究本身。
因此,面对这种困境,我试图具体地围绕杨小凯和他《牛鬼蛇神录》(以下简称为《牛》)等著作为主要分析对象,以他个人的经历和思想历程来管窥这些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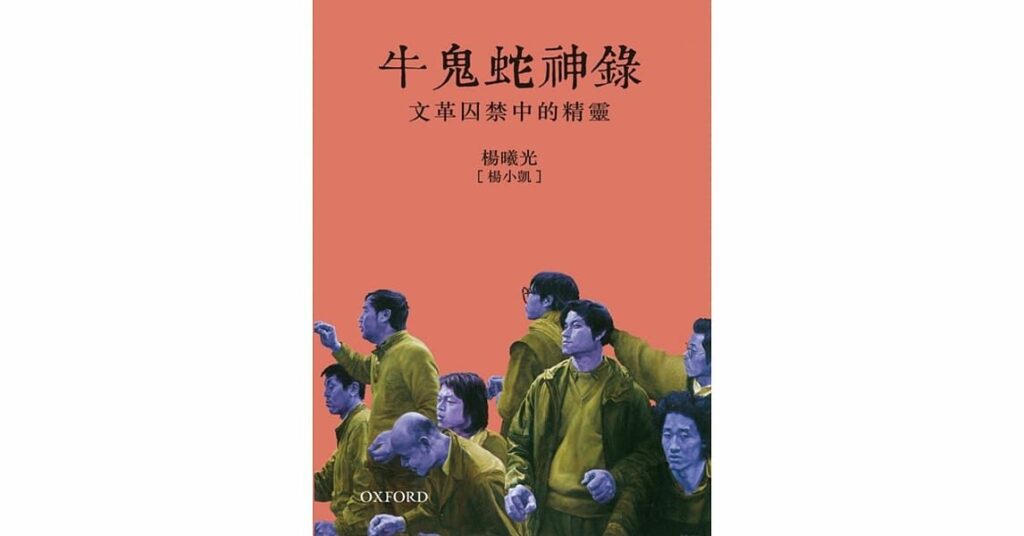
杨小凯:《牛鬼蛇神录:文革囚禁中的精灵 》(牛津大学出版社,2016)
在思想史的叙述中究竟有几个「杨小凯」,是否杨小凯思想的差距,以至于我们不得不作为「两个杨小凯」来对于他的前后思想进行分类?
作为思想史事件的《牛鬼蛇神录》
事实上,在杨小凯去世后的纪念文章中,就已经呈现了不同立场的人对他的诠释,「革命者」、「反革命者」、「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异议者」、「宪政主义者」、「经济学专家」、以及寻求超验维度的「基督信徒」等。尽管这些标签所描述的都呈现出了杨小凯某些特定时段的一些特征,但是却同样在「官方」和「非官方」各自暗含的意识形态叙述的立场下,没有深入探讨杨小凯乃至他所处的整个时代处于怎样一种思想变动和连续性。只有梁捷在《杨小凯的两张面孔》超越了这种断裂的、标签化的叙述框架,指出杨小凯思想的连续性,「小凯一生,只关心大问题,大学问。他能进入经济学,也正因为胸中包含着中国发展的大问题。」
在这篇文章中,我的基本观点是,长久以来,对于文革到当下的思想而言,在「官方」和「非官方」二元主导叙事背后,却共享着以把握「客观历史」为基础,试图建立一种真理性的历史解释和价值判断的冲动,都消除着对于历史事件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理解。然而,在解读杨小凯的文本时,我们会发现,在杨小凯对于文革及其后来事情的叙述是不同于这些价值判断的主导叙述,而是呈现出了复杂性和多样性。

杨小凯,原名杨曦光,经济学家。
事实上,《牛》具有几个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对于研究文革和后文革思想史,它提供了一位深度参与到湖南造反派运动的亲历者的见证和反思,最为难得的是提供了关于看守所、劳改队和监狱的宝贵历史材料。此外,与其他类似的文革回忆著作(如王学泰《监狱琐忆》)非常不同的是,杨小凯的思想立场似乎发生了对立性的巨大转变,从「无政府主义」、「平等派」、「激进革命者」转变为了倾向于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保守派,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很多不知内情但却知道杨曦光和杨小凯的两个人的人,绝不会接受他俩是同一个人的『假说』」 (页3)。
这也就延伸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在思想史的叙述中究竟有几个「杨小凯」,是否杨小凯思想的差距,以至于我们不得不作为「两个杨小凯」来对于他的前后思想进行分类? 值得注意的是,在《牛》书中的第一章「中国向何处去?」中,甚至杨小凯自己都是以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混用的方式来进行论述,在一开始,杨小凯都是以第一人称论述,而在讲述因为1978年刑满释放后无法找到工作而改用自己的乳名时,他写到「从那以后,杨曦光这个人就在中国消失了,而杨小凯却… …被人知道。(页4)」这种叙述的特殊性,让人注意到了一个诠释学的视阈问题,也就是杨小凯自身的「历史意识」是如何理解自己,并对于文革中那个「自我」经验进行叙述和诠释的问题。
而对于研究者而言,就必须回答这里中所展现的「两个杨小凯」之谜,即《牛鬼蛇神录》这本书究竟是「过去那位杨曦光」的思想还是如今这位「杨小凯」的思想,或者是一种反思性的融合诠释。这是需要读者和研究者本身再进一步诠释和说明的过程。一旦我们阅读《牛》同时期杨小凯的其他学术著作和随笔时,会不时发现同样的思想和文字呈现散落在这些文章之中。
因此我们要处理的一个思想史的问题就是,杨小凯的思想,是否如大多数人甚至他自己曾经说的,是完全的一个断裂,或者相反,事实上还是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呢。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其实并不是单单为了理解杨小凯,而是以杨小凯为例,扩展到一个更为广阔的思想史领域,那就是在文革乃至当代,对许多诸如「革命」等主题的理解是以非此即彼的方式来解读,还是其中具有二元论对立者们所忽视的延续性和复杂性。
他点名指出当时湖南几位常委以及全国官僚的「权力无限大」,而革命人们完全丧失了权力,大批被投入到「公检法控制下的监狱」。
杨曦光与《中国向何处去》
杨小凯曾回忆他撰写《中國向何處去》(简写为《何处去》)一文的背景是他从小受到的教育让其对革命英雄主义充满崇拜,然而自己的父母在文革开始就遭到批判被定性为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也迫使他没有加入保守的组织「联动」而是在长沙一中参加了反对派「湘江风雷」。不幸的是,在1967年的「二月逆流」中,他作为造反派被当局关押了一个月,出狱后参加串联,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酝酿出了这篇文章。
在1968年1月12日,他以署名「省无联一中红造会钢三一九兵团《夺军权》一兵」发表了《向何处去》的征求意见稿,而后刊载于同年3月的(广州)工革联印刷系统委员会的《广印红旗》上。这篇文章的背景是发生在文革1967年1月和2月之间两个重大事件。在当时被「左派」称之为「一月革命」和「二月逆流」。在67年1月,首先在上海,以工人为主的造反派夺取了上海市党政机关的权力,并且在1967年2月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后由改名为「革命委员会(革委会)」),这一事件影响到全国,陆续出现了地方造反派成立革委会夺取行政权力的行动,并且也成为了各地,特别是湖南、重庆等地大规模武斗的导火索。
而「二月逆流」则是同年2月,中央层面内部老干部派与文革派在两次政治局会议上的权力斗争,最终也影响到各地「造反派」和原来党政机关之间的政治博弈。杨小凯将其描述为当权派对造反派「采取了最急切的残酷镇压手段」,最后,「财产(生产资料)和权力从革命人们手中被夺回到官僚们手中,」他点名指出当时湖南几位常委以及全国官僚的「权力无限大」,而革命人们完全丧失了权力,大批被投入到「公检法控制下的监狱」。杨在这篇大字报中不仅直指周恩来为「红色」资本家阶级的总代表,用陈伯达和江青的立场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而且也对当时的「革委会」并不彻底的革命性提出了批判。
朱敬一專文:對岸中國,往何處去?
《何处去》的行文很明显受到马克思和毛泽东以及当时大字报风格的影响,整篇文章围绕毛泽东在1966年5月7日写给林彪的信 「五七指示」所展开。毛在「五七指示」中提出了军队要成为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创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
而《何处去》一文,杨小凯将其发挥是毛对于「中华人民公社」的构想,指出这并不是一种空想的乌托邦,而是避免苏联修正主义道路的科学。然而《何处去》一文真正与「五七指示」不同的是加入了权力斗争和暴力革命的内容,这也是导致杨小凯入狱的直接原因之一。对于杨而言,实现「中华人民公社」首先是要推翻已经形成的官僚机构,让工农兵都摆脱官僚控制,因此,此时的杨小凯将自己划归为「极左派」,要通过暴力最终建立真正人民自治的公社。
这篇文章中,杨小凯也表达了自己对于革命和改良的理解。在他看来,造反派成了的革委会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是「罢官革命」的产物,「这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使文化革命前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统治逶迤曲折地变为资产阶级官僚和几个陪衬的群众组织代表人物的另一种资产阶级的统治,而革命委员会就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物。」杨小凯认为自己所在的「省无联」造反派尽管是「新生的幼芽」,但是确实群众的自发组织,并且强调不能够把「革委会专政当成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最终目的」,而是提倡一种始终需要进行暴力的不断革命论。
让人遗憾的是,杨小凯写到,随着张九龙的枪决,「那看不见摸不着的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也带到坟墓中去,将一些永世无法找到答案的迷留给人间。
《牛鬼蛇神录》的革命和反思
杨自己在《牛》一书对于为什么写《何处去》一文的事后反思是,他因为在当时遭到迫害,「希望找一种理论来支持自己的政治利益或使其在马列正统理论基础上合法化,而马克思关于民主主义的观点及反特权反迫害的观点,自然成为他的思想武器。(页8)」在这本书中,杨小凯呈现了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对于文革和革命的看法,提供给读者更多理解文革和革命的视角。
有趣的是,如同杨后期的《中国经济史笔记》一样,事实上,这本书中仍旧有他在写作时期进行经济学研究的主题,特别是劳动分工(页134)。杨甚至提到了一些与当下主流叙述甚至文革研究所不同和忽视的观点与内容。比如,在《圣人君子》一章中,「君子」这位前湖南大学的数学教师陈老师,也是指导杨在监狱中阅读的老师之一,其政治见解就不同,「他预见毛泽东一死,江青等激进派会与共产党内的保守派官僚发生冲突。如果激进派成功,中国可能有机会彻底改变共产党制度,甚至爆发革命。如果共产党里的保守派占上风,中国又会回到苏联体制,长时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机会。(页140)」而在后来的文章中,杨小凯自己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甚至假设过保守派和江青为主的激进派进行内阁制衡的思想实验。
而在描述地下革命家张九龙的故事时,杨小凯写到,张九龙说「人民反对当局的革命情绪像性冲动涨落一样有一定的周期,民主国家让这种冲动不断地发泄,所以很少能形成革命的形式。而共产党国家没有让革命情绪发泄的通道,这种情绪就会积累起来,形成革命形势。」 (页56-57)因此张认为,这种文革,动乱反而有助于巩固政权。而杨却不认同这点,即尽管上层操纵下面的两派,「但下面的人不也在利用上层的冲突在追求自己的利益吗?……文革中两派形成的社会背景是智商与当年英国圆颅党和辉格党之间的冲突及法国山岳派与立宪派的冲突非常相像。(页57-58)」但让人遗憾的是,杨小凯写到,随着张九龙的枪决,「那看不见摸不着的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也带到坟墓中去,将一些永世无法找到答案的迷留给人间。(页60-61)」
还有一个故事则反映了在社会底层,文革也具有着并非意识形态斗争而是残忍报复的层面,杨小凯通过劳改犯扒手向土匪讲的故事展现了其野蛮性。在文革期间,由劳教就业人员组成的「长沙青年」此时得到了报复公安干部的机会,一名叫「三毛伢子」的把曾经审讯他的干部的眼睛挖去。杨这样写道:
向土匪的故事使我震惊和不安,因为我一直认为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政治冲突是由政治观点的冲突引起,虽然我比别人更注意这种政治冲突背后的社会矛盾,但我不会想到,对于向土匪的小团体而言,这种根深蒂固的阶级仇恨和互相迫害却不需要任何政治意识形态,它是赤裸裸的互相迫害和报复。我有时用《双城记》中的故事安慰自己,造反运动中民众的暴力都是由革命前社会上层阶级对下层民众的系统暴力迫害引起的,正像法国大革命的残暴的一面是由当年贵族的残暴引起的一样。这位长沙话都讲不好的扒手使我了解到革命中黑暗和无理性的一面,使自己那些看上去高雅的政治意识形态黯然失色。 (页67-68)
而在论述他和保守派的成员毛火兵之间的私人友谊时,杨小凯说到了因为是对文化革命的幻灭感,「这场曾经是人民的『盛大节日』的革命造反从来没有给人带来任何好东西,我的激进的理想主义也早就幻灭,这大概是我们友谊的真正基础。(页85)」
杨小凯不仅对于革命本身所带来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实际上也反思了革命者参与革命的动机本身。他在《宋导演》中讲述过湖南省话剧团的造反派领袖导演宋绍文的故事,宋因为牵涉到「省无联」的案子而被以「反革命黑手「的罪名判了15年。在狱中为了减刑却不时出卖狱友,也举报过杨小凯,差点导致杨的加刑。但是在文革结束被平反后,让杨小凯奇怪的是,在1979年民主运动中,宋又卷入其中,甚至出谋划策,杨小凯对此的总结是,」他是有某种追求轰轰烈烈和英雄主义的精神病,正像偷窥狂和露阴癖是精神病一样。 (页256)」因此,杨小凯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更为丰富社会图景,并非简单二元论迫害者与被迫害者之间的关系,而是复杂的每一个人都可能对他人残忍的相互伤害的社会。事实上,杨小凯也提醒人们即便是参加「革命」的人,动机也并非都是单纯,而是怀着各种的利益和动机,甚至也是一种革命的精神病态也可能成为参加者的动力。正如法国大革命的维尼奥所说的「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上面的这些描述,实际上也表达出了杨小凯在写作这本书时,对于革命的理解。在革命的非理性浪潮中,参与其中的人的动机是多样的,而并非单纯革命的目的那样简单,甚至在革命意识形态的掩饰下是真实的人的欲望和仇恨。从而这也导致了亲历者杨小凯对于激进革命的一种幻灭。
「我是太渺小的个人主义者,我害怕专制和革命带给我的痛苦。但如果我是个不关心功利的历史学家,我会说,专制制度,革命的历史地位却是件比功利远为复杂的事情。」
「两个杨小凯问题」:断裂还是延续
上面已经提到《牛》一书的特殊性在于,他是杨小凯中年之后成为专业经济学家其思想逐渐成熟所写的一本回忆录。在流传的关于杨小凯的文章中,几乎都将杨小凯分成了杨曦光的左翼激进思想和后期杨小凯的右翼经济保守主义思想。即便是此时的杨小凯本人也将杨小凯和杨曦光无论是在写作的叙事上还是政治立场区分了开了,似乎呼应了1990年代开始的「告别革命」以及「思想淡出, 学术凸现」的潮流,但是我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牛》这本书本身,还是在梳理杨小凯中后期所写的文章和研究论文,杨小凯的「革命意识」的思想并不是一种断裂和消退,而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呈现了出来。
首先,杨小凯将自己的经济学体系强调的「角点解」的超边际分析和劳动分工理论,视为是一场经济学的思想「革命」。杨小凯在ARE(《美国经济评论》)和JPE(《政治经济学期刊》)等最优秀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过多篇文章,出版过经济学教科书的专著,他将自己的理论视为对过去基于边际理论的新古典经济学提供了变革。在他的几本经济学教科书中,杨小凯在导论中都列举了哥白尼日心说体系取代托勒密地心说体系的例子,认为自己试图做的事情,「同哥白尼和开普勒做过的事情相似。通过恢复专业化和分工问题的主流经济学核心中的应有位置。」(《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页13)。遗憾的是,在杨小凯去世后,近年来主流经济学已经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实验经济学等更为微观和实证的基础上,远超出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畴,杨小凯提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范式并没有如同他期待的那样产生广泛的影响力,但是有一点可能肯定,杨小凯在自身的研究中仍旧延续了「革命意识」冲动,期待的不是过去理论上的修正,而是一种颠覆性的革命。这种「革命意识」的不仅延续在了杨小凯所从事的经济学研究中,实际上在他思想的反思和批判中,也呈现出了同样一种复杂的变化和延续性。
杨小凯大约在1987年前后(写《牛》一书同时期),写了一篇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在1999年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一次研讨会的发言稿《中国宪政的发展》杨小凯也做了类似的发言。),一方面他指出了文革的复杂性而不是简单的否定或支持,并且延续了上面提到的张九龙的观点,指出「文革的作用正是在人民中培养起强烈的反革命情绪。」事实上不仅没有改朝换代的可能,相反是巩固的政治权力,因为「人民自从大跃进依赖对专制政体的不满在文革中发泄掉了…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今天利用上层冲突触发革命的机会比以前要小得多,这是文革的积极后果之一。」与此同时,杨小凯也补充了自己反对革命的原因并不是从历史角度出发,而是从个人角度,「我对革命和专制制度的否定完全是从一种功利主义立场出发,而不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我是太渺小的个人主义者,我害怕专制和革命带给我的痛苦。但如果我是个不关心功利的历史学家,我会说,专制制度,革命的历史地位却是件比功利远为复杂的事情。」
在1999年杨小凯在一次访谈中(〈革命與反革命及其它〉),他进一步修正了他对于革命的看法:
现在我要修正这个观点,因为革命理论也有其合理性。我认为,有些东西在学术上还没有定论,你不能轻易地说,反革命的理论就是对,或者革命的理论就是对的。革命对统治者总是一种威胁,没有这种威胁,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承诺就不可信;有威胁,其行为就不会太离谱。美国宪法明确指出:人民的权利是天赋的,而政府的权利是人民给的。所以美国人普遍认为:你要统治我们,就必须得到我们的同意。要是你搞得不好,人民就可以革你的命。如美国的弹劾制度,就是人民表达革命权利的一种方法。你是否读过已故的奥尔森的书,他就有非常深奥的革命理论,认为一个稳定的秩序会使既得利益者寻租行为制度化,而革命和动乱却能打破制度化寻租。美国很多经济学家都很敬佩奥尔森。他甚至把社会动乱看成一个国家兴盛的原因(见他的「国家兴衰论」) 。他大概是西方的「多难兴邦」 论者。
纵观杨小凯从1990年代到临终前的文章,除了他引以为豪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范式外,他所关注的最主要的问题仍旧是革命和社会转型问题,即如何进行一个社会的转型和利益分配,以及用什么样的手段和方式来进行社会的制度安排。无论是他吸收理解的哈耶克思想,还是在他与萨克斯,胡永泰合作的论文《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以及未出版的《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等都将关注点放到了如何通过如何通过宪政所保障的个人权利,特别是私有产权来作为自由市场的基础来保证成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
在不同的文章中,杨小凯已经不再提倡自己年轻时所赞许的「法国大革命」,而是对英国「光荣革命」不吝赞美之词,他认为「光荣革命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虚君宪政,议会民主制度使政府对公平的政治游戏规则和法律制度的承诺成为可信……」从而杜绝了「国家机会主义」。
尽管杨小凯对于西方制度的演变和发展所阅读的经济学之外的文献非常有限,大多数都限制在制度经济学的框架之内,比如对于「光荣革命」的理解主要依赖于诺斯(North Douglass )和温格斯特(Barry R. Weingast)在1989年之后所发表的文章,他也意识到自己作为经济学家而不是专业历史学家的局限。因此,他会对于自身知识的局限也有所反思。如上文所见,他会严谨地修正自己的观点,强调只是从自身经验和个人功利主义的角度对革命抱有了保留的态度,但是他并非完全的否定了革命的意义,而奥尔森的《国家理论》则让杨小凯看到了革命积极的一面,就是打破无法通过渐进改良形成的长期寻租制度结构。
这些论述都呈现出在「两个杨小凯」的区分中始终具有着深层的延续性和共同的问题意识和关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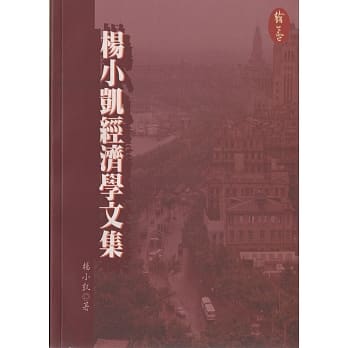
《杨小凯经济学文集》(翰芦,2001)
在我们这个告别革命,思想淡出,民主制度衰败的后疫情时代中,也许仍旧是一种爝火不息的召唤。
思想史脉络中的「两个杨小凯」诠释
在面对杨小凯思想表面的对立和内在的连续性中,我们可以放在一个更为宽阔的思想谱系里来进行理解。
在「革命」一词主导中国近现代上百年的时间中,无论是对其趋之若鹜还是避之不及的人,常常都会以二元论的方式,非此即彼地理解「革命」及其附属的词语。例如「革命」与「改良」,「启蒙」与「救亡」、「法国革命」与「英美革命」等等,完全忽视了两者之间具有的有机联系,而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在脱离历史和文献语境的情况下,成了各种意识形态和立场之争,这也成为了上个世纪90年代思想界喋喋不休的主线。
其次,「两个杨小凯」背后还涉及到着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在当代历史和田野研究中,如何对文本和口述档案进行选择和鉴别已经成为研究者重点讨论的问题之一。由于时间性,当事人本身也会从自身当下的背景对于记忆性的材料进行加工和选取。具体到中国现当代历史的研究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官方档案可信度和可用性不足或限制的问题,尽管口述历史和个人回忆录可以作为一个补充,但是文本的可靠性和适用性仍旧需要具体的进行讨论。
因此研究者不仅需要在官方和非官方多种主导性叙事中进行甄别,还需要在极为有限的资料中,进行多角度复杂性的呈现,因为随着一些档案和个人淹没在主导性的历史叙事和诠释中时,后来的研究者甚至无法找到可供对话的研究问题,甚至被动的延续占据公共话语权的主导性叙述的路径进行讨论,从而不仅没有呈现出历史和历史诠释的多样性、可对话性和复杂性,而是强化了少数几种能够在公共领域允许讨论的叙事模式,导致了对真实问题讨论的遮蔽。因此,杨小凯的整个思想脉络的意义不仅是给予我们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可以用的视角和文献来研究文革和文革后社会和知识史。杨小凯生命中所呈现出来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的思想变化中实际上仍旧有同样的问题意识和精神的探索。
在这里,我尝试用阿伦特(注:Hannah Arendt,汉娜 · 鄂兰)《论革命》中提出的类型来解释杨小凯思想中的连续性。阿伦特洞见性地区分了革命和解决社会问题两者之间所具有的不同目标。革命的真正的目标是以自由立国,并且革命是政治崩溃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而革命作为一个解放问题通过释放在苦难社会中人的痛苦和愤怒,也会产生出破坏性的力量。因此,革命无法解决社会问题,也就是贫困问题。相反,人们一旦运用革命的政治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反而会导致恐怖,而正是恐怖把革命送上了绝路。
在这个动态基础上,阿伦特指出了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真正的不同在于,法国革命一开始就偏离了自由立国的基础,不得不被历史包袱中人民的痛苦和无休止的同情所左右,从而释放出暴力。而美国作为「新大陆」没有不平等和社会苦难的历史包袱,因此,革命的方向始终以自由立国和建立持久制度为目标。在阿伦特看来,真正解决和缓解社会问题的并非通过革命,而是技术(页78及其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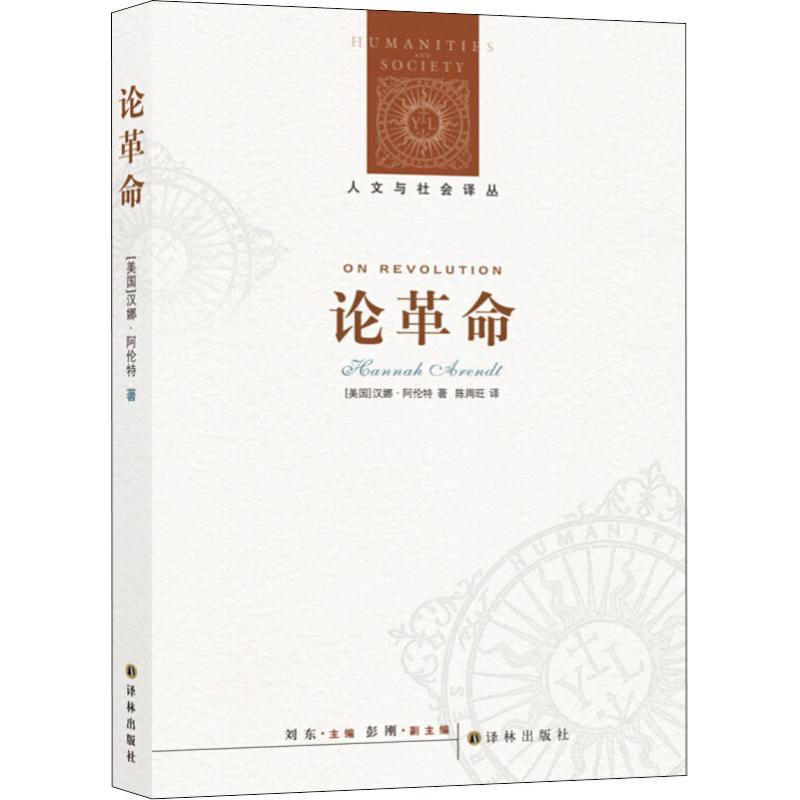
汉娜 ‧ 阿伦特:《论革命》(译林出版社,2011)
正如梁捷所指出的,「中国向何处去」作为一个问题意识而言,无论是对于作为造反派的杨小凯还是经济学家的杨小凯,乃至生命晚期皈依基督教的杨小凯都是终身求索的一个问题。因此,「革命」和专业技术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看似矛盾的两者之间,在杨小凯的一生的思想经历中却得到了统一。他始终对自我立场处在一种严谨的批判性反思之中,并且不断地纠正着自己的观点。杨小凯晚年对于「革命」的理解,尽管保持着警惕和保留,也反对「职业革命家」,而强调需要做一个能在自由民主制度下有生存技能的公民,但是杨小凯也和阿伦特一样,指出了「革命」在历史中重要的意义和目标,以及对于既定寻租化制度的颠覆。而杨小凯所走的道路,在某种意义上并非告别「革命」,而是在解决「社会问题」但是这两者背后却是同一种激情和关怀在推动。
尽管杨小凯离开他所关怀的这个世界已经十多年,中国乃至世界的制度结构和思想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论他之前的各种论点和理论是否成立和实现,人们可能持有不同的看法,也许我们可以批评他对于西方世界历史和社会仍旧持有很多简单化的理解;也可能好奇,如果他还活着,会对特朗普时代的「宪政危机」和如今宪政——民主的衰落,自由市场所带来的不平等加剧会有什么样的看法;然而,至少我们可以认为,杨小凯在某种意义上,在我们这个思想贫乏、充斥着意识形态争论和争吵喧嚣的时代中,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思想资源,也值得未来的研究者来进一步诠释和理解一些我们自身胆怯与刻意忽视的东西,这种力量并非因为占有了更多的客观材料,在期刊上争取了多少话语权力和引用,而是对我们和我们这个时代的批判性反思和诠释。
当杨小凯在出狱时,他写到「我心中充满着对未来的向往和不安。但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我一定不能让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种种动人心魄的故事消失在黑暗中,我要把我亲眼见到的一段黑暗历史告诉世人,因为我的灵魂永远与这些被囚禁的精灵在一起。(页411)」在我们这个告别革命,思想淡出,民主制度衰败的后疫情时代中,也许仍旧是一种爝火不息的召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