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洛杉矶大火,众口一致骂「左」;俄乌战争,批俄批乌皆有,自然俄罗斯这次是侵略者,西欧美国的态度皆不是看点,普京输掉则俄罗斯可能解体,反而是后续看点,也即俄罗斯将又一次跟「苦难」相遇,或许便如帕斯捷尔纳克早就哀叹过的:「我仅仅是让全世界,都为我的家乡俄罗斯的美丽哭泣。 」一有机会,我就会谈《日瓦格医生》这本书,因为它的意义,换到中国和中文语境中,在于乱世如何守住做人的底线,尤其一个知识人,虽不得不随世道险恶而沉浮,但是不害人不作恶,不随从权势整人、牟利、构陷,即使做个好人,也不必强出头抗恶,而是行善、扶弱济贫、施展不忍之心,那就是《日瓦戈医生》这本书对当代中国的意义,回首反右、文革、六四、盛世这六十年,便知此绝非易事,偌大神州有几人?第二点,此书说出斯大林「集体化」的残酷,令苏联人拼搏纳粹德国视死如归,因为他们反正是死。一部小说写到这种深度,也超越了人性,而具有普世性,中国小说或历史研究,离此境差得还远。 】
《日瓦戈医生》,据经典介绍,是一部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小说波及了1903年夏到40年代末近半个世纪的俄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触及了道德、政治、哲学、美学、社会、宗教等一系列问题,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具有广阔的历史容量、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容量的长篇作品。它最初被苏联禁止,后由一位意大利出版商带出苏联,而苏共总书记苏斯洛夫亲自飞往罗马,要求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干预,因为出版商是意共党员,而他竟提前退党,于1957年出版了意大利文版,1958年成为西方最畅销书,并获诺贝尔文学奖。
一、小说
八九前在国内有没有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的中译本?蓝英年的译本是1987年出版的,我到海外才看到,因为在网络上,还是一个残本,中间缺章,反而更加勾魂。我到美国后,最早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外面的那条拿骚街上的一个旧书店里,买了一个英文本,吭吭哧哧读了很多遍、很多年,也是唯一我啃过英译本的外国小说。
小说对男女主人公,有某种近乎雌雄分体的并列叙述主线。尤里,一个医生兼诗人,幼年丧父,寄人篱下,一生披肝沥胆,受尽苦难,最终几近暴毙街头,却坚忍不拔地追求真理和幸福,他是那样一种人:他们不是英雄,也没有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在极端状况下,他们既有不坠世俗的真诚、善良、纯真,也有坚韧执着的信念。
如果换到中国和中文语境中,一个知识人遭逢乱世,身处黑暗之中,如何守住做人的底线,虽不得不随世道险恶而沉浮,但是不害人不作恶,不随从权势整人、牟利、构陷,即使做个好人,也不必强出头抗恶,而是行善、扶弱济贫、施展不忍之心,那就是《日瓦戈医生》这本书对当代中国的意义,回首反右、文革、六四、盛世这六十年,便知此绝非易事,偌大神州有几人?
女主人公拉拉,才是本书的第一主角,也是精神丰富、内涵复杂而深广的俄罗斯本身的隐喻,多灾多难的俄罗斯女性的象征。日瓦戈如此浩叹:“俄罗斯,他的无可比拟的母亲,这是具有不朽光辉、历经灾难、作不可预卜之险的俄罗斯,是名扬四海、顽固、奢侈、疯狂、不负责、殉难的、可敬爱的俄罗斯。”虽然老帕将他对俄罗斯的痴迷移情于笔下的拉拉,令人有坠入西方女性主义之嫌,但是我的感觉,却是相较于日瓦戈一颗永远的稚童之心,拉拉则远不是只有“妇人之仁”。这种张力,其实也是这本书的魅力所在。
这本巨著,与其说它延续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大小托尔斯泰的知识者命运的俄国文学传统,不如说它是在宏大历史中演绎“爱情的受难”,十月革命前后俄罗斯大地上发生的战乱、变革、宗教、人性、多重恋情等等,都不过是老帕疯狂文学野心的烹饪材料:“我仅仅是让全世界,都为我的家乡俄罗斯的美丽哭泣。”
书的结尾处,末章有一段议论很有趣,是借着日瓦戈的朋友戈尔东的嘴说出来的:
“集体化是一个错误,一种不成功的措施,可又不能承认错误。为了掩饰失败,就得采用一切恐吓手段让人们失去思考和议论的能力,强迫他们看到并不存在的东西,极力证明与事实相反的东西。由此而产生叶若夫的前所未闻的残忍,由此而公布并不打算实行的宪法,进行违背选举原则的选举。
“但是当战争爆发后,它的现实的恐怖、现实的危险和现实死亡的威胁同不人道的谎言统治相比,给人们带来了轻松,因为它们限制了僵化语言的魔力。
“不仅是处于你那种苦役犯地位的人,而是所有的人,不论在后方还是在前线,都更自由地、舒畅地松了口气,满怀激情和真正的幸福感投入严酷的、殊死的、得救的洪炉。
“战争是十几年革命锁链中特殊的一个环节。作为直接变革本质的原因不再起作用了。间接的结果,成果的成果,后果的后果开始显露出来。来自灾难的力量,性格的锻炼,不再有的娇惯,英雄主义,干一番巨大的、殊死的、前所未有的事业的准备。这是神话般的、令人震惊的品质,它们构成一代人的道德色彩。”
原来四十年代反法西斯战争中苏联人的视死如归,竟是因为同二三十年代斯大林大清洗的恐怖相比,战争相对还要算轻松的,这是希特勒纳粹德国遭遇顽强抵抗的一个从未被历史解释过的苏联式的内因,也显示出历史的复杂、迷惑以及细节远非学术可以穷尽,或许这也使得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不靠特务恐怖便无法维持统治。
二、作者
鲍里斯.列.帕斯捷尔纳克,犹太人,文化造诣极高,其父是美术、雕塑、建筑学院教授、著名画家,母亲是著名钢琴家,他从小受家庭熏染,对欧洲文学艺术造诣很深,精通英、德、法三国语言,他自己既有诗人天赋,又受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影响,曾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后转入历史哲学系,一九一二年夏赴德国马尔堡大学攻读德国哲学,研究新康德主义学说,并非一个普罗作家。
中译本最早的译者蓝英年,有一本回忆录《历史的喘息》,是中文里极少见的老帕的介绍,说他性格孤僻,落落寡合,与那些新作家格格不入,一度布哈林欣赏他。二战后苏联文坛宽松,他在1946年开始写这本书。此时,他也认识了奥莉加.伊文斯卡娅,蓝英年称之为“帕斯捷尔纳克的红颜知己”,也是小说中拉拉的原型。后来就是她把小说交给意大利出版商菲尔特里内利,在意大利出版。
此书脱稿后被苏联当局封杀,苏联作协长期敌视和批评他,以致意大利出版《日瓦戈医生》后,又被诺贝尔文学奖选中,他竟不得不拒绝接受,晚年染上忧郁症,孤独死去。他一生的隐喻,就是诗人勃洛克所说的“我们是俄罗斯恐怖时代的儿女”,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形容这本书说得更彻底:“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回来搅扰我们了。”
从俄罗斯文学的脉络来看,苏俄有两个托尔斯泰,老的叫列夫,乃旧俄大文豪,其文学位阶,不逊于莎士比亚,在图拉省庄园写的《战争与和平》,几乎是世界名著之冠;小的叫阿列克谢,生涯恰处于新旧交替的乱世,承俄罗斯文学之遗续,却并未开启苏联文学之端倪,他有一个《苦难的历程》三部曲,《两姐妹》、《一九一八》、《阴暗的早晨》,战乱中小布尔乔亚的挣扎,是从老托小托到帕斯捷尔纳克的一个不变的主题,从《战争与和平》到《日瓦戈医生》);小托更描摹苏俄变天之大惊怵,在故事中经营主角们从苦闷彷徨走向革命觉醒。
但是,日瓦格医生在1911年十月革命的时候并不是一个革命的反对者,当街上出现被沙皇马队砍杀的游行示威者的时候,他奋不顾身地去抢救革命者,后来他只为了坚守内心的那一点信念,和革命发生了冲突,革命以粗暴的方式蹂躏他,他承受不反抗,也绝不沉沦,这就是他的人道主义,也称人文主义。所以帕斯捷尔纳克是超越了两位前辈的。
三、电影
其实中国人最早接触《日瓦戈医生》,不是小说而是电影。
赫鲁晓夫列此书为禁书,也无缘拍成电影,却给了《阿拉伯的劳伦斯》的英国大导演大卫.连恩一个机会,拍了一部史上最高票房大片。电影改编应是非常成功,将小说繁复多头的线索简化,凝聚到尤里和拉拉的几度重逢又离散;从彼得堡到西伯利亚,革命灾难中一男二女(日瓦戈妻子冬妮娅)的悲欢离合,以及瓦雷金诺雪屋的烛光、雪原狼嚎,还有电影的主题曲,以俄罗斯三角琴弹奏,隽永无比。结尾落在他们遗失的孩子并不知道自己是谁,那种语言已经用到尽处的沉重,摧人心肺。
自然,这部电影讨好,在于它是所谓“西方话语”而非“俄罗斯话语”,也不是对苏俄革命的暴露才受欢迎,而是把一个西方式的故事放到俄国动乱环境里去再现,主题是人性问题。这种知识分子式的乱世情爱,是西方文学的一大正宗,大红大紫的《英国伤员》也是这种题材。至少西方传统的看法,乱世是一个可以超越道德约束的外在强制,仿佛越是道德的人在此越可以被道德赦免,由此便越见人性的生动和真实。
另外,此剧其实具有很浓厚的女性主义色彩,主人翁是拉拉而不是尤里,作者写她以女性承受男性权力的欺压,与科马洛夫斯基的关系暗示着旧俄制度的蹂躏,其丈夫巴沙是新制度的象征则遗弃了她,只有尤里这么一个旧知识分子懂得爱她,这是此片的要旨。
(文章转自作者脸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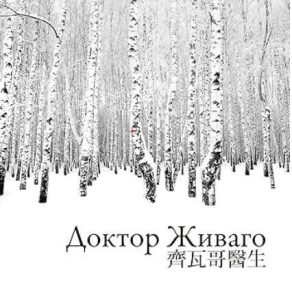
附:
天寒地冻时刻,总让我想起《齐瓦哥医生(Doctor Zhivago)》,因为导演大卫.连(David Lean)真有本事,冰天雪地、冰柱霜栋的每个画面,让人看得浑身打寒颤,却又被齐瓦哥医生和爱人Lara的恋情给暖着心。
当然,作曲家墨希斯.贾赫(Maurice Jarre)的音乐更是发挥了煽情与撩情功能。
电影改编自俄国作家鲍里斯·巴斯特纳克(Boris Pasternak)的同名小说,时代背景就在俄国共产党革命夺权前后,所以一开始是打算采用俄罗斯音乐做背景。
1960年代,「冷战」方炽,反共题材当然不可能到俄国拍摄,只能改在西班牙取景。拍摄前,大卫.连几乎听烂了各种俄罗斯音乐,好不容易听到了一首合适曲子,就带着音乐到拍片现场播放,让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能体会他所要诠释的音乐情感。甚至,Maurice Jarre到达西班牙拍片现场时,大卫.连也开门见山告诉他说:「我要的音乐就像这首曲子一样,请你就照这首曲子的曲风来作曲吧!」
人算不如天算,后来,出品的米高梅公司担心这首俄罗斯民谣版权有问题,大卫.连才勉强同意放手让Maurice Jarre去作曲。但是第一次交出的作品,大卫连露出一脸很痛苦的表演,什么也没说,墨希斯知道不行,回房间再去写。
第二版完成,大卫.连说话了,他说:「太悲伤了!」退货。
第三版完成,大卫.连的评语是节奏不对。但是他不要墨希斯再写了。他直接对墨希斯说:「你带着女朋友到山上去玩玩吧。」
大卫.连的理念很简单:心头要有爱情滋润,笔下就会有爱情光采。
果然,休假有用,恋爱有用,就在爱情的滋润和抚慰下,墨希斯写下的「Lara’s Theme 」凄恻委婉,深情动人,让这段不伦之恋成就了很多人艳羡的乱世浮萍。
后来再由著名填词家Paul Francis Webster填上歌词,改名「Somewhere My Love」上市,顿时红遍半边天,也是一代歌王Andy Williams最爱颂唱的流行名曲。成为影史名曲。
「Lara’s Theme 」/「Somewhere My Love」
作曲:Maurice Jarre
作词:Paul Francis Webster
《蓝色电影院》
「每日一曲」021
—蓝色电影笔记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