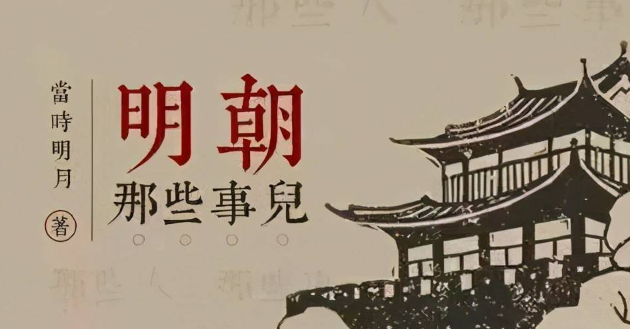近日在推特上看到老周横眉发出的关于当年明月之传闻的一则推文:
近两天都在传《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石悦(笔名:当年明月)被抓进精神病院了,说是打了男领导,猥亵了上级女领导……
推文配了两张截图,一是当年明月暴得大名的成名作《明朝那些事儿》的书籍封面,一是其标准照和简介。x.com/laozhouhengmei/status/1876960873610399765
笔者算是个历史文化的业余爱好者吧。《明朝那些事儿》刚热起来的时候,特意买来阅读过。实话实说,除了感觉其叙事比较轻松诙谐,具有明显的网络文学特征,并未留下特别深的印象。但我开始留意和关注作者这个人。
青年才俊,名利双收
不可否认,石悦具有明显的才华和优秀的悟性,也是勤奋之人。其大学并非历史科班出身,能够坚持和发展自己的个人兴趣爱好,算得上性情中人。
笔者记得有媒体报导,《明朝那些事儿》曾居全国十大畅销书之首,三年销量突破1000万本(套),当年各路学者、名人争相推荐,包括中共央视等各路媒体争相报道;作者曾经连续七届荣登中国作家富豪榜,2007年不到30岁时,就有稿费版税收入达4000多万元,而到近年还有数千万元未结算。作者还先后获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明史学会副研究员等头衔。20多岁就因一部作品出了大名,赚了数千万稿费,实现了财务自由,也获得众多荣誉头衔,可谓名利双收的青年才俊。
官场得意,步步高升
石悦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00年考取公务员,进入顺德海关成为一名小职员。在其因《明朝那些事儿》暴得大名后受到提拔,他也入了中共党组织,先是调入海关总署一本杂志做编辑,后又在宣教中心综合室任副主任,并到河北某县挂职任副县长;再往后出任某中字头文化公司副总经理;2018年出任山东省政府办公厅综合处处长;2020年调任上海市外宣办和新闻办副主任,并在其后一年任政研室副主任。40岁多点时,他已经官至副厅级。
可以看出,石悦是典型的中共特色国成功人士,其从湖北宜昌的一个小镇做题家成功突破阶层壁垒,由广东顺德而一步一步到京城,到大上海,在体制内混得风生水起,入党提职,步步高升,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智商、情商双高的他,能适应体制,顺应体制,利用体制,正是钱理群先生所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中共特色国屡见不鲜。
特色体制,毁人不倦
石悦的升迁和任职地域与上海市长龚正有高度重合。据传正是龚赏识他,一路提拔,改变了他的命运。众所周知,中共官场与历朝历代没有本质区别,要升迁发展必须要有人身依附或裙带关系。特色体制里的官员需要自己的班底人马,石悦因才华被龚正赏识和吸纳完全可以想见和理解。
但从作品可以看出作者石悦毕竟是个有才情有个性的性情中文人,其擅长历史小说并不一定适合公文体写作。他的性情和精神可能受到体制的压抑甚至扭曲也是完全可以想见和理解的。据传其调查报告等就常不受龚的认可,而他也无可奈何难以适应。
财务自由的石悦完全有条件离开酱缸粪坑的体制,却对体制恋恋不舍,又修炼不到“人精“的境界,做不到完全始终如一异化自己的人性、人格。精神无所依仗,灵魂四处游荡,难免文人无行,大概率会人格分裂甚至精神分裂,也就酿成其今日之悲剧。
当然,他不可能是李宜雪那种被精神病的受迫害者。所以,笔者推断,网络传言大致不虚。
工具理性,价值糊涂
当年明月安在哉?石悦的经历遭遇无疑具有中共特色国典型的社会学样本意义。但笔者还要从其阅历和作品本身引申,略谈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以及对历史文化的现代价值判断问题。
其实我们可以从作品一窥作者的价值观。“当年明月”的笔名出自宋代晏几道的《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中的词句“当年明月在,曾照彩云归”,可以看出石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好和认可。他熟读中国史书,尤其是明史,其认知视野和价值观深受中国传统儒家出世经世济世的影响,这也解释得通其热衷官场宦途的原因。他在《明朝那些事儿》中还特别推崇张居正、王阳明等,真不能排除其有“帝王师”的想法和野心。作者出身基层公务员的家庭背景,以及大学年代与初入社会进入体制时,正是中共改开新洋务运动高潮的江胡时代,其知识结构和认知基本不具备周有光先生所倡导的“多从世界看中国”的格局,与1980年代胡赵主政时期的教育及社会文化氛围已不可同日而语,正是中共“工程师治国”大行其道的年代,正是国家社会充斥工具理性而不问价值理性的年代。所以石悦的认知里理所当然地基本不具备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观,而是以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为底色及中共特色体制的工具理性为主,价值理性稀里糊涂甚至阙如。多年来,笔者目力所及,石悦这类文化人可以说比比皆是,见怪不怪了
《明朝那些事儿》对史实材料的选取和叙述的铺陈、渲染,故事性较强,其实可以当着小说来读。这也是一般读者觉得无阅读障碍,因而大卖的原因。但从故事性和真实性体验来说,莫言、余华、陈忠实等的小说更佳,而且真实性体验更具震撼力和冲击力。这也是笔者后来基本不看中共国出版的历史作品而宁愿读小说的主要原因。
再则,在史实的逻辑梳理表达方面,该著基本乏善可陈,阅读收益与二月河的帝王三部曲类似,更无法与钱穆、余英时、高华、秦晖、吴思、刘仲敬等学者比拟。当然,此种比较对并非专业学者的作者要求难免过高,但这是笔者的真实阅读体验。
在史观、史识方面,该著水准与二月河并无二致,只不过腐朽的帝王权力崇拜、成功学及大一统崇拜没有那么明显突出赤裸裸。与二月河的作品一样,从该著也基本看不到在现代文明视野下对人物、人性善恶是非的现代观照和价值判断。
笔者20多年前到深圳后,陆续读过一些港版、台版的历史书,大大拓展了知识视野,提升了认知能力,尤其在价值判断上,可以说脱胎换骨了。这是读《明朝那些事儿》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阅读体验。
对待历史和文化,笔者近年更趋向保守主义,甚至某种程度认同钱穆先生所言,须对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持温情的敬意。但这并不是失缺是非善恶的普世、普适坐标,而是在尊重史实前提下持守恒定的价值判断标准。
也许我们不宜对当年明月要求过高,他毕竟是中共特色体制长期教育驯化的产物。但惟其如此,更显悲哀,所以不吐不快!
作者 艾地生
2025年1月16
【光传媒首发,转载请标明出处:www.ipkmedia.com 】
【作者文章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