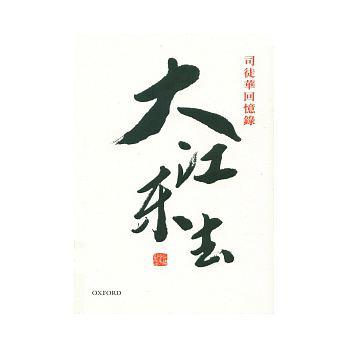hari Matters 20250223 转自:新世纪
儿时在乡间的生活悠闲而快活。绿油油的田野,清清河水流淌、我和兄弟姊妹常常走到屋前的小河,时而捉鱼时而玩水,但安宁的背后,却是个国难日深的日子。一九三一年,我岀生那年,中国爆发九一八事件;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本军队占领香港,母亲和保姆兰姐领着我们、一行九人在饥饿和刺刀威胁下离开香港,回到广东开平故乡避难。这是我第一次离开香港,踏足中国。
这趟回乡的路程相当艰苦,父亲为了赚钱养我们,被迫留港。母亲背着娟女,兰姐背卫干,家姐背婵女,明哥、我和阿强互相照应下走路回乡。以今日的交通计算,坐车三、四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但当时却要好几天的时间。我们农暦年廿三起程,本想赶回乡下过年。那日从西环坐朋友的机动帆船(俗称「电扒」)去唐家湾(在今珠海),中途遇上大浪,刮大风又下大雨,非常狼狈。泊岸后,当地人十分善良,收留我们睡地板过了一夜。翌晨,天气已明显转冷,同时下着微微雨,我们一行人小孩多,无法起程,等了数天,天气还没有好转,实在不想打扰人家过年。幸好,母亲记三婶的娘家就在石岐,步行两日即可抵达;途经南塱时,明哥想起这里是初三班主任许桂生老师的故乡,按址找到了他,却因其家地方太小,无法收留我们过夜,但亦慷慨地煮了大盘番薯让我们果腹。露宿一晚后,翌日再步行至石岐,走了不久,大家都非常疲累,我和明哥要背行李,不到十岁的阿强实在累得不能再走,犹幸遇到一位好心的同乡,他用单车把阿强载走、相约在石岐等候;年三十晚终于抵达石岐,接过阿强后便暂住三婶家,在当地过年。当时日军已经占领石岐,设有不少岗哨,中国人路过时必须急急行礼,动作稍为慢点,就会挨上拳脚,这些日军甚至施展柔道,把他们像摧生鱼般凌空摔在地上。我们沿途尽见日军之残暴,也见到路边堆满冻死、饿死的同胞,我年纪虽小,但已有愤慨之情。
过了两天,我们吿别三婶,准备登船回乡。临行前,明哥带我去购置干粮。甫走出店子,被几个人抢去一包大饼,打劫的人并没有立刻走开,干脆站在原处狼吞虎咽,吓得我们口瞪目呆。记得那时我们家人带着铁镬走难,人家还说意头不好,或许就应在这桩事上吧。
我们由石岐坐船到江门,转船去三埠,再由三埠返到乡下赤坎时,已经是年初七,从香港逃难的这段路程足足走了两个星期。回到东华里向东村的祖屋,母亲便病倒了。她经常肚痛大作,除请医师治理外,有迷信的乡民,教我们用吸盘吸母亲的肚子减轻痛楚。这俱为诬诞之言,毫无科学根据。母亲的病一直没有好转。
当时,父亲独自留香港工作,并察看局势,吩咐我们继续住在乡下。父亲曾在乡下读过两年书、到香港后学师修整机器,复升大偈一职。后来他还搞些小生意,把旧汽车的机器拆下来,装在「电趴」中出售。父亲为人甚讲义气,有一班好兄弟跟着他,例如安叔、吴坤等,后来都成为父亲的伙计。
母亲的病况急转直下,到一九四二年四月与世长辞,才三十八岁,据说是死于子宫颈癌。按照俗例,母亲弥留时女儿不能陪伴在侧、爸爸吩咐明哥陪着母亲,还在她跟前念《金刚经》。母亲下葬时,我们依照乡例,边跪边送,家姐伤心过度、喊着不肯跪、说母亲还没有死去,娟女那时刚好弄伤膝盖,膝痛令她每跪一步都喊得特别凄厉,我们兄弟也哭如泪人。那时乡下适逢疫症,霍乱横行、死了很多人;加上战乱,饿殍遍野。不少乡人只能吃番薯叶充饥,或将一些木瓜树锯下来,吃里面嫩的部分。木瓜树通心,愈近中心愈嫩,易于咽食。种种情景,于今忆起,仍觉悲凉。
母亲过身后一年,父亲续弦,祖母托媒人替他找填房。家姐大表反对,父亲劝她说,弟妹要有人照顾,家姐则反驳说:「你需要一个老婆,我不需要一个阿妈,我愿意终身不嫁,照顾弟妹。」最终,还是拗不过父亲,他娶了张雅嫦做我们的继母,我们唤她阿婶,她与家姐年纪相若,但家姐对她十分冷淡。
即使是走难期间,父母亲对我们的教育仍是十分重视。在乡下赤坎,明哥插班读初三,考试科科一百分;家姐在校内是风头趸,既是话剧第一女主角,也是篮球校队成员,动静皆宜;我和阿强入读小学。明哥初中毕业后升读越秀中学高一,我小学毕业后则在开平县立中学升初一。
一九四四年夏,日军向故乡进攻、占领了三埠后稍歇。七月,我们一家避走赤水,贝距三十多里的赤坎,到九月时已坚壁清野,实施戒严,俨如死镇。父亲因病,需就近向一位不肯撤离的医生求诊,便留在镇内。我随学校到塘口墟暂避,那是母亲的娘家。那时我念初中第三年,家姐带着我,跟数名同学合租一间屋,住了差不多一年。每逢周末,我便步行二十多里路,冋赤坎探望父亲,歇宿一宵后,翌日才返回学校,顺道带走一星期的食粮、诸如米、豆豉、柚皮等等。
过去,父亲鲜有谈及往事,但那年大抵因为镇里那股萧索气氛使然,父亲在多个周末晩上,每每在孤灯下、病榻侧,断断续续忆述他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代。虽然父亲没有诉说祖父不生性,但从他的言谈间,我总觉得祖父活脱脱就是乡人所讥的二流子。当时只得十二岁的父亲孤身来港谋生,还要接济家乡众口。我隐约知道,父亲在一九二二年曾参加香港海员大罢工,后来便回乡娶了母亲。母亲是文盲,她的哥哥是马来亚华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失去了联络;她妹夫是美国华侨,在三藩市唐人街磨豆腐、发豆芽,得享天年。一九二五年,省港又发生大罢工,父亲响应回乡;一年多后,罢工结束,他便带同母亲来港生活。
一九四五年,战争已经接近尾声,但日军暴行未止,父亲担心我们安危,决意安排我们分批回港,年纪较小的阿强跟着赤水的超叔去澳门、明哥和家姐则自行赴澳门二叔处暂避。父観、我和其他弟妹暂留乡下。到抗日胜利,父亲和明哥分别从乡下和澳门返港会合。我记得他们说,返港之时,香港仍是军政府年代,英申未完金接管,街上人很少:只有三轮车、十分萧条。当时,战败的日军仍未撤退,我们亲眼目睹他们被俘虏、当扫街工作、在马路旁挖臭泥、途人为了泄心头恨、不时向他们掷石块。到此穷途末路,他们也只有把头垂得低低的。
战时,我肄业于乡间的开平县立中学,位于族人聚居的赤坎,所以姓司彼的同学为数不少,单名者很易同姓同名,连我在内,班里就有四个「司徒华」,其中一位是女同学。班任为避免四人的习作、试卷、成绩等混淆,便要大家改名字、分别选了「桦、骅、铧、哗」四字,老师尤把「桦」分给那女同学,其余的三个字,由三个男的抽签。
我抽得「骅」字,很是高兴;抽得「哗」字的,十分懊丧,常被同学取笑。他很不服气,翻了字典,查出「晔」和「烨」两字,要求老「哗」字,改为「晔」或「烨」,但老师并不接受,反斥责一番说:「晔」或「烨」两字的读音是「业」,不是「华」,不能改。这老师未免霸道、其实「哗」读「娃」,属阴平,与属阳平的「华」,也不同音。从此,我们四人在习作和试卷上,名字都要写有偏旁的「华」字、以免掉乱;至于点名时则更有趣,不是叫司徒华,而是「司徒木华」、「司徒马华」⋯⋯ 到后来因为毕业证书附有照片,不会弄错,大家又回复「司徒华」的本名了。
开平县立中学的校歌,事隔数十年,我还记得歌词:「百足山志、白云悠悠」。因为学校与百足山遥遥对望,而「潭江源远,赤水归舟」,讲的都是家乡沿途风景。这一段学校生活,最难忘的是义务劳动。学校分配给每班一小块土地种瓜、豆和蔬菜。同学们利用课余时间播种、浇水、施肥、去草、除虫。瓜、豆,蔬菜长成后,摘下来在午膳时加菜,大家都吃得特别甘甜。冬天,全校总动员,绕着校园挖一条小运河;到了春天,校园面对的潭江的江水涨了,就把江水引进小运河来。这样不但加强了保安,为所种的瓜、豆、蔬菜浇水,也缩短挑水灌溉的路程。
日军占领期间,我们曾经数度迁校,才可以继续上课。那时,我亲历日军及伪军下乡抢掠,所以每日清早,我们就要带着干粮,走上山暂避,直到天黑,才敢下山。每次回到家中,所有东西都被翻乱,食器用具统统打烂,甚至有缺德者在饭锅上留下粪便。
离赤坎大概两、三里路程,有一座碉楼,即今日开平的南楼,扼守潭江水陆要塞,那时候,乡民自发组成自卫队轮流守护,监察日军的快艇。每当日军来到,便听到打锣声响,提醒老弱妇孺走避、至于坚守碉楼的卫士,则用土炮跟日军对抗。有一晩,我们听到日军和自卫队激战,炮声连绵,但乡民武器始终有限,敌众我寡,被日军在其他地方登陆及包围,以催泪弹连番进袭,并攻入碉楼,将七个卫士杀死,最惨无人道的是将他们生劏,一个一个挂在树上,警吿我们不要抗日。现在南楼的七烈士祠,就是为纪念他们这段义行而建的。
这些耳闻目睹的抗战事迹、给我很大刺激。我渴望国家富强,不会再被侵略,人民不再被异族欺压、点点的民族爱国思想、由此生起。一九四五年,战争结束,我回到香港,才十四岁的少年,已留心报章的时局消息。诸如重庆谈判、国共内战等等。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以为中国从此富强,人民会得到幸福,但后来的发展、却是民族陷入一场又一场更大的灾难。这一切一切,令我有更深的反省和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