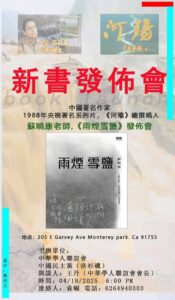
【《雨烟雪盐》由台湾出版社印刻文学出版,2025年3月25日在台北正式发行。作为一部兼具思想深度与感情温度的作品,《雨烟雪盐》为读者提供了多重维度的阅读体验:既可将之视为流亡岁月的私人回忆,又可从中领悟中国现代史的兴衰寓言。苏晓康在书中实现了自我心灵的和解——从最初的悲痛欲绝到最终的淡定坚守,他用文字走过了一条救赎之路。同时,他也为六四一代知识分子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让后人得以窥见他们的内心世界和思想轨迹。对中文读者而言,阅读此书不仅是了解一段特殊历史经验,更是一次反思自身与时代关系的启迪。雨、烟、雪、盐四味杂陈,仿佛寓意着苦难与希望交织的人生图景;而苏晓康以不灭的写作热忱,将这图景生动地呈现在我们眼前,留给我们长久的思索和感动。 】
被迫流亡海外的苏晓康,是整个「六四一代」知识分子的缩影。 1989年,他与其他参与民主运动的知识分子一同背负「动乱幕后黑手」的指控,被政府通缉,不得不逃离祖国。自此开始,他展开了长达36年的异乡漂泊。在这期间,他尝尽了「无家可归」的滋味——远离故土、语言环境隔阂、社会身份失落,这些都构成了流亡者共同的困境。苏晓康一度隐居于美国特拉华州僻静小镇,过着孤寂而清贫的生活。对他而言,流亡者最大的悲剧不只是失语或寂寞,而是精神上的沉沦。因此,尽管现实艰难,他始终努力保持精神上的清醒与坚守。他投入海外民运媒体工作(曾任《民主中国》网站主编),并持续写作反思中国的历史和现况,以此对抗流亡生活的空虚感。
《雨烟雪盐》正是苏晓康流亡三十余年心路历程的缩影和见证。书名寓意他在流亡中尝到的百般滋味:「雨烟」象征台湾这片文字原乡给予他的温湿气息与文化滋养,而「雪盐」则象征北美漫长严寒的孤独岁月。正如编辑陈健瑜所概括的,苏晓康的经历宛如「穿梭在无数极端之间的摆荡」,经历了气候的剧变(热带的焦灼雨幕与北美的冰雪严寒)、人际的离散(骨肉分离与异乡结交)、身心的伤病(车祸重创、抑郁困顿)以及全球政局的震荡(时局荒诞多变)。在劫后余生之余,他始终没有放弃内心深处的信念,用笔墨抵抗精神的堕落,体现出「茫然不放弃之心,在黑暗中匍匐爬行」的顽强意志。可以说,苏晓康以一己之身经历并书写了流亡知识分子的典型遭遇:失去祖国怀抱的痛苦、文化身份的游离,以及肩负传扬真相的使命感。他的故事映照出整整一代流亡知识人的挣扎与坚守:即使身处他乡,他们仍试图为中国的历史伤口作见证,为真相发声,拒绝让记忆被扭曲湮没。
「大骨架」与「私人心境」交错的叙事结构
《雨烟雪盐》的叙事结构独具匠心,在「大骨架」与「私人心境」之间交替穿插。苏晓康一方面以宏大的历史视野搭建叙事骨架,追溯中国现代历史的曲折循环;另一方面又深入描写个人内心的悲欢离合与细腻情感,使全书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次上来回切换、相互映照。全书共分六章,每章各具特色,彼此之间形成历史与情感的双重奏:
第一章〈暗世烟蒙〉:聚焦于动荡黑暗的世局中人心的不屈。 「基辅烽火连天」的战乱记忆浮现,苏晓康从中看到人性在黑暗中的坚贞高贵。这一章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和历史气息,在阴霾弥漫的世界图景下点出微弱却炽热的人性之光。
第二章〈泪愁阑干〉:画风一转,回到作者个人经历的内在世界。经历短暂如春之新生希望后又陷入崩塌般的愁苦——或许指的是妻子复健希望的破灭,或人生再次遭逢变故的痛楚。这一章充满私人化的眼泪与哀愁,情感浓烈细腻。
第三章〈神圣殿堂〉:重返大历史的视角,苏晓康揭示流亡圈内一些现象的荒诞不经。他讥讽所谓「流亡度假村」与「养士」的现象,点出某些自命不凡的政治殿堂其实荒唐可笑。这里他以犀利的观察力,解构了海外民运和知识圈中的矛盾与问题,带有强烈的批判意味和讽刺色彩。
第四章〈乡村醒来〉:再度回归个人层面,记述他从特拉华迁居华府过程中的点滴。在劳神费心的搬迁之后,妻子傅莉在忧郁的暮春中逐渐「苏醒」——这暗示傅莉的身心状态出现好转或心结逐渐打开,使苏晓康得以倾吐许多过去不敢言说的心声。这一章充满生活气息和家庭情感,语调较为舒缓内省。
第五章〈垦荒列传〉:又一次转向广阔的历史场域。苏晓康描绘了一批「在天使与魔鬼间拔河」的异议人士形象。他透视六四之后整整一代中国流亡者的命运悲剧——那些满怀理想出走的人,在海外拓荒般地追求民主自由,却也不得不在理想与现实、道德与诱惑之间挣扎。人物众生相的刻画背后,其实隐含着对历史的大视角审视:这代人的悲剧正是中国现代史悲剧的一部分。
第六章〈灵动难眠〉:作为全书的尾声,苏晓康回望起点——他当年的代表作《河殇》以及震撼人生的「六四」事件。三十多年过去,再谈这段历史,依然有说不尽的疑问与迷思萦绕在心。这一章史诗般地将私人记忆与民族创伤交织在一起,充满对历史循环与命运的省思。
透过上述章节的交替铺陈,《雨烟雪盐》形成了双线并进的叙事节奏:一条线索是横贯古今的历史反思与时局评述,另一条线索则是个人生命史的深情告白与心灵独白。苏晓康善于在宏大叙事与个人叙事之间切换自如,使读者既能鸟瞰广阔的历史风云,又能贴近一个流亡者细腻的内心世界。这种结构,实际上延续了他早年「全景式、立体式」报告文学的写作风格——他曾以记者般的眼光审视社会全貌,同时又不放弃对人物命运的深入描绘。而在《雨烟雪盐》中,苏晓康将这种风格进一步融合入散文式的自传体叙事,文体既有纪实的力度,又有抒情的温度。大骨架提供了历史深度和思想张力,私人心境则赋予作品情感共鸣和人性光彩,两者相辅相成,使作品兼具思想性与可读性。
劫难中的心路与写作救赎
苏晓康从1989年六四事件后开始长达三十多年的流亡生涯。在此期间,他经历了家庭重创:1993年的一场车祸让他与刚团聚不久的家人再度分离,妻子傅莉重伤昏迷一个月,清醒后全身瘫痪,仅一手可动并失去语言能力。面对这沉重打击,苏晓康形容自己当时的状态是「一个精神瘫痪的人,陪护着一个体能瘫痪的人」他内心几近崩溃,却仍须日夜照料失去自理能力的妻子。在漫长的照护岁月里,苏晓康承受着强烈的愧疚与悲痛,不断自我拷问。 「我非常非常内疚,某种程度上这成了我的动力,因为我认为是我造成的」、,他懊悔妻子为陪伴他流亡而放弃国内医生事业却遭此厄运。然而,写作渐渐成为他疗愈精神创伤的方法。在近乎绝望中,他没有选择沉沦,而是重新拾起笔杆,以文字寻求心灵的出口。正如他日后所体悟的:「现在,悲痛成为我一种力量使我可以去写比我以前还好的文字」。这种将悲痛转化为创作动能的历程,让写作对苏晓康而言不仅是纪录,更是自我救赎——在「诡谲世局与多舛命运」之前,「唯有书写能完成自己」。透过不断书写,苏晓康将深重的个人伤痛倾注笔端,既抒发了内心的压抑,也赋予苦难以意义。他在创作中融入血泪与真情,实现了心理上的救赎,为自己在黑暗中点亮一盏心灯。
苏晓康在书中不仅讲述个人故事,也借此折射出中国近代历史如同「圆圈游戏」般的循环往复。他深受哲学家李泽厚观点的影响,认为中国现代史总在重复相似的戏码——朝代更迭、运动起伏,看似风云变幻,实则常绕回原点,令人徒叹历史的戏弄例如,他曾指出,习近平执政下中国正在「思想上回到毛泽东、制度上回到文革以前、经济上回到大锅饭」,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回圈。在《雨烟雪盐》中,苏晓康以流亡者的视角,冷峻地观察这种历史循环。他所描述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圆圈游戏」暗示着:历史并未因时间推进而自动进步,反而有可能在不同形态下重演过去的错误。这种认知为作品增添了强烈的政治寓意——它提醒读者反思当下中国的道路是否又走回了老路。
与此同时,苏晓康采取了「人物—历史双重化」的叙事策略,透过双重书写将个人经历与历史兴衰紧密相连。在他的笔下,每一个具体的人物故事往往具有双重意涵:既是个体命运的展现,也是历史宏图的一部分。例如,傅莉作为作者妻子,其遭遇固然是私人的不幸,但在苏晓康的书写中,她身上也投射出一代中国知识女性的命运缩影,以及专制时代中个体尊严受损的悲剧。再如,他在〈垦荒列传〉中描绘的那些流亡异议者,既是他亲身结识的朋友同道,也是「六四之后一整代中国流亡者的悲剧」象征。每个人的故事都不再仅仅属于个人,而是被提升到了历史寓言的高度。苏晓康善于通过这种双重叙事,达到「小中见大」的效果:从个人故事中读出历史走势,于细微处体察政治气候。
这种人物与历史的双重化,在文学表现上体现为丰富的隐喻与象征运用。例如,傅莉在车祸后二十多年始终无法释怀自己的残障,直到某天她虚构出「自己当年曾清醒地帮助控制失控汽车、拯救全车人」的情节,作为给自身苦难一个神圣意义的解释。苏晓康在书中记录了妻子这一心理转折,并感叹道:「她必须为自己所承受的终身痛苦,提供一个最大化的神圣因由」,这其实也是人在面对无法改变的悲剧时,一种自我救赎的本能。他配合地称赞妻子为「救命恩人」,让她终于放下心理重担开怀大笑。这里苏晓康透过一个家庭内对话的小场景,传递出更深层的象征意义:个体需要赋予苦难以意义才能继续生存,正如一个民族需要为所经历的灾难找到历史的意义才能继续前行。傅莉自创的「救人」理由,如同中国民众为历次苦难(如文革、六四)所赋予的意义一般,是一种带着虚构成分的心理寄托,但也是真实的人性需求。苏晓康将这层寓意通过文学化的笔触巧妙写出,令人读来既为夫妻间的深情所感动,又引发对更大历史命题的思索。
整体而言,《雨烟雪盐》的文字蕴含丰富的政治隐喻。那些书中出现的「流亡度假村」、「天使与魔鬼拔河」等语汇,都带有讽刺和寓言的色彩,影射着海外民运圈内部的矛盾、人性的光明与阴暗交战。苏晓康一方面歌颂流亡者坚持真相的勇气,另一方面也不讳言人性弱点对理想事业的侵蚀——这种不加粉饰的书写本身就具有政治清醒意义。在历史的层面,他揭示中国百年来「江山易帜」而本质未改的怪圈;在人物的层面,他则呈现理想主义者如何在现实中碰撞挣扎。文史双线交织之下,读者能强烈感受到作品的政治寓意:它是在警示后人,没有反思的历史必将重演,没有自省的个人难逃悲剧。苏晓康以文学为载体,寄寓了他对中国历史和政治的深沉思考,令人深味其中。
「六四」一代的精神图谱与书写传承
将《雨烟雪盐》置于「六四」知识分子的文化脉络中,可以发现它延续并典型展现了这一群体的精神图谱与写作特质。苏晓康本人是1980年代中国「新启蒙运动」的先锋之一,当年以尖锐的报告文学和《河殇》电视片叩问民族灵魂。六四之后,他与众多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被迫远走他乡,但思想探索的脚步并未停止,反而将反思的触角延伸至更广阔的历史文化层面。在海外,他们继续关注中国的命运,书写中国的故事,形成了独特的流亡叙事传统。
苏晓康的创作可谓这一传统的缩影和高峰之一。 《雨烟雪盐》中渗透的强烈家国情怀、反思精神以及自我剖白,正是「六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共有特质。
首先,这一代人具有深刻的历史责任感和问题意识。他们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沉疴积弊有清醒认识,喜欢追本溯源、反省文化。例如,苏晓康早在《河殇》中就大胆批判过民族性的局限,而在本书中依然延续着对「中国近代历史圆圈游戏」的思索。这种执着于历史反思的笔调,是「六四知识分子」文化基因的一部分——他们试图从历史中寻找答案,探究中国为何一次次错失变革良机,民族的前途路在何方。
其次,他们的精神图谱中有强烈的悲剧意识与人道关怀。经历六四挫败后,理想主义者们难免幻灭,但他们并未放弃对人性光辉的信念。苏晓康在书中对人性的描写既不乌托邦也不犬儒,而是带着悲悯:既看到人性的软弱(如傅莉漫长岁月里的绝望与逃避,也赞美人性的坚韧(如傅莉最终愿意直面现实、接受依赖活下去)。这种对人性的复杂体认,正是六四知识分子在巨大历史悲剧后获得的成熟。他们不再热衷于高调口号式的英雄叙事,而转向朴实真诚的个体叙事,用一种近乎忏悔和见证的方式来书写。正如评论者所称赞的,苏晓康的作品是一份「有血有泪的谦卑诚挚告白书」——没有矫饰,只有真诚。这份诚恳与自省,在六四一代的写作者如刘宾雁、余杰等人笔下也能见到。他们以文字记录内心的疼痛与思考,拼凑出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地图:迷惘、痛定思痛,却又不肯放弃对自由真理的向往。
再次,苏晓康的写作样态也代表了六四流亡作家的典型风格:文体融合与跨界书写。许多六四后的知识分子并非纯文学作家出身,他们往往横跨新闻、史学、文学等领域,例如苏晓康既是记者、政论家,又是文学书写者。因此在他们作品中,常见纪实与虚构并存、论述与抒情结合的复合文本。 《雨烟雪盐》正是如此:既有新闻记者式的见闻记录,也有小说般的场景描摹;既包含议论评论的段落,又饱含散文诗般的抒情。例如,书中既引述方励之夫人李淑娴的箴言「我们这些人必须让真相在身后不被歪曲」来点明事实书写的使命感,也穿插了作者个人对命运的梦呓与诗意感怀(如「春雨梨花之唐诗意境」的美妙比喻)。这种写作方式打破了严格的文体界限,读来虽像回忆录,又如历史随笔,更有小说的故事性和戏剧张力,充分展现了六四知识分子融思想深度与文学表达于一体的追求。
作为「六四」知识分子群体中的重要一员,苏晓康用《雨烟雪盐》勾勒出了这一群体典型的精神风貌和写作样态:肩负历史记忆、坚守知识良知,融合理性批判与感性自述。他的文字既有对国族命运的执着关切,也有对个人灵魂的反覆拷问;既延续了八十年代启蒙思潮的批判勇气,也展现了经历挫败后知识人特有的冷静与深情。这使得《雨烟雪盐》不仅是苏晓康个人的生命之书,更是整个六四一代知识人的精神写照。
(文章转自苏晓康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