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風 Matters 5 月 7 日
十一月四日凌晨,二十二岁的大学生周梓乐从停车场的三楼坠落,四天后在医院离世。示威者表示他遭到警察追捕,但没有证据能证实这项说法。周梓乐是首位在抗议现场身亡的示威者,这让社运人士群情激愤。他的照片遍布了整座城市,人们在大学校园、街角处和公园留下字条与蜡烛追悼他。十一月的第二个周末,人们在公园举行了大型的烛光悼念仪式,纪念坠楼身亡的周梓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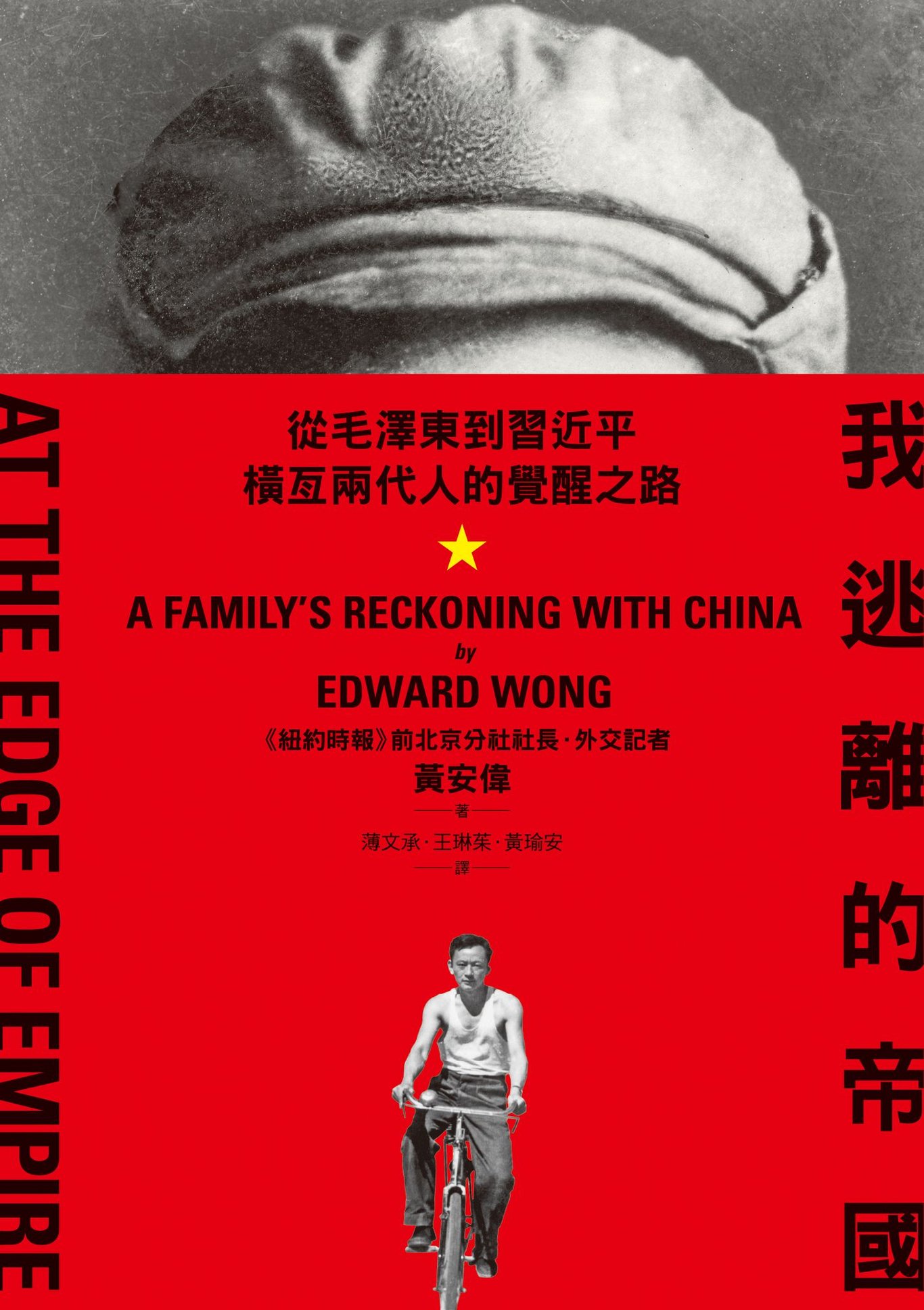
香港.二○一九年
二○一九年十一月的温暖午后,身穿黑色忍者服装的年轻女子站在大学校园里空荡的户外游泳池池底,将玻璃瓶一个接一个扔向墙壁。每个瓶子都碎开来,玻璃碎片散落一地。她每扔一次都会调整目标。墙上的其他地方也有黑色的痕迹,那位女子的同伴用他们自己的瓶子在这里朝墙壁练习投掷。他们将那些瓶子装满汽油并用火点燃了。墙上的烧焦痕迹显示出这些自制炸弹击中的位置。这些都是为了模拟真正的目标:香港警察。
在泳池边缘的地面上,有两位学生正朝靶心射箭。他们就像那位女子一样,身穿黑色服装,戴着口罩。我一早在香港理工大学散步时注意到的气味,这里也闻得到。那是汽油的味道。在校园的几个地方,学生堆满了装有汽油的瓶子,里头塞着布条或是报纸。我曾看到许多纸箱里装满了上千个汽油弹,准备让人点燃并投掷出去。
在学生眼中,他们的敌人是曾经备受香港市民爱戴的香港警队。示威者表示,警察现在是依照中国共产党和远在北京的统治者行事。自一九九七年以来,这些统治者强化了对香港警队的控制,起初是渐进式的,但近年来速度不断加快。他们肆无忌惮的举动导致香港居民的愤怒和恐惧持续升温,例如二○一五年中国的国安人员绑架了香港的五名书商。现在看来,中国曾经向英国和香港居民承诺的「一国两制」似乎将在二○四七年(也就是英国政府将殖民地移交给中国领导人的五十年后)正式结束之前就面临瓦解。
我看到地上写着「Fuck the Popo」的英文标语。这里的「Popo」指的是警察,校园里的学生李傲然(Owan Li)解释道。 「示威者必须面对警察的暴行,」他说,「中国共产党是完全独裁的政权。他们的心态是要维持完整的主权与统一。他们会说只有政府及其统一与主权才是最重要的。谈到人权、人民的权利或人民的生活时,他们不屑一顾。而维护主权的唯一方式就是独裁统治。」
在校园的其他地方,我看见两位年轻人正在将金属把手焊接到大块的黑色金属板上。他们在打造盾牌。有人在墙上用喷漆画上了反法西斯图像小说与电影《V怪客》中的V符号。在另一面墙上,学生们喷上了「如果我们毁灭,你们也将与我们同归于尽」(If we burn, you burn with us)的字样。这是《饥饿游戏》(The Hunger Games)小说中的弓箭手女主角凯妮丝.艾佛丁(Katniss Everdeen)所说的台词,这本小说讲述的是反抗威权国家的故事。我到处在校园里闲逛,看到更多学生在练习射箭。
在过去一周,学生和其他示威者占领了香港各地,目的是扰乱交通,强化他们反警察和反共产党的诉求,希望香港或北京的官员能做出让步。但警方已经展开反击,他们毫无顾忌地用警棍和催泪瓦斯直接对付示威者。到了周末,学生在香港各地的五所大学校园筑起了路障,其中反抗意志最坚决的一群学生聚集在香港理工大学。他们准备展开最后一战。数个月来的抗议、高喊口号和街头冲突,最终演变成了这样的局面。
五个月前,在六月的时候,这座城市的居民开始上街抗议,人数之多是数十年来从未见过的。他们对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希望立法会通过的《逃犯条例》感到愤怒。许多香港居民担心,如果中国的安全机构想要缉捕香港的特定人士,无论是批评共产党的人或是企业主管,这项法案将为地方当局开辟一条新的途径,让当局能够将香港居民送往中国大陆接受起诉和监禁。在示威者眼中,这项法案是共产党用来破坏香港法治的工具。在今年夏天的示威活动中,参与者并不仅限于学生,不同于五年前我曾经目睹的雨伞运动示威。那时候,示威活动围绕在学生于金钟地区建立的营地。今年夏天,遍及全城的示威游行吸引了年轻人、老人、高中生、上班族以及退休人士。
整个夏天,警方与示威者之间的冲突规模和暴力程度不断升级。警察发射催泪瓦斯,并逮捕了许多人。一名女子被警察发射的布袋弹击中脸部,导致眼睛严重受伤。这些事件广为人知,许多示威者都描述了这些事件,显示出警察采取的残酷手段。林郑月娥在九月时宣布撤回《逃犯条例》,但到了那个时候,引发抗议事件的原因已经远远不止于此。示威者要求整个警队必须承担责任,而这支警队曾经受到多数香港居民的敬重。示威者持续提出五大政治诉求,包含全面落实双真普选、撤销被捕示威者控罪,以及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以彻查警方滥权。
我在华盛顿观察情势的发展,当时我在《纽约时报》担任外交记者。我一心想要回到香港的街头,而不是和政府官员一起喝咖啡或参加大使馆晚宴。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新闻学,接着到哈佛大学担任研究员之后,我在二○一八年搬到华盛顿报导川普政府,这是许多美国新闻机构当时最关注的新闻。这是一趟返乡之旅,我可以再次与父母共度时光,而爱月也在开始上小学时认识了她的祖父母以及堂兄弟姊妹。从我的国际新闻报导职涯来看,这种发展也有其逻辑:首先报导美帝在伊拉克计画的重大挫败;接着关注美国最大挑战者中国的崛起;现在则探讨美国民主从内部权力核心遭到侵蚀的问题。然而我也感到失落:我不再是真正意义上地「身临其境」,在报导美国外交政策时,也不再沉浸于其中所涉及的国家与文化之中。
在二○一九年十月一日中国国庆日前夕,中国大使馆批准了我为期一周的签证,让我前往北京采访国庆的重头戏,也就是习近平即将主持的天安门广场阅兵仪式。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七十周年的宣传大秀,但我认为这或许是能让我一窥习近平权力的机会。更重要的是,结束后我可以前往香港,亲自了解这场运动。
十月一日,北京城仍在沉睡时,我在广场西侧的军事博物馆搭上了官方巴士。太阳升起时,我们越过广场,来到我们的座位。昨天晚上睡前,我打电话给父亲,想听他描述他当年在一周年阅兵仪式上于毛泽东面前游行的事情。我在二○一五年参加习近平的第一次阅兵仪式时,我们还没有谈过这件事。现在我知道了父亲在这里的经历,我感觉自己就像跟随他数十年的幻影,化身为他早年在帝国中心广场上存在的回响。
自毛泽东以来,共产党领导人从未在四年内举办过两次阅兵仪式。此举本身就突显了习近平的野心。去年,共产党将「习近平思想」写入党章,这是另一个与毛泽东的相似之处。这次的阅兵仪式与二○一五年大致相同。习近平身穿传统的无领外套,搭乘黑色轿车从天安门出发,经过一列长长的军队队伍。他检阅了战车、飞弹与无人机,其中有些是首次公开亮相。他们揭开了东风-41型导弹的神秘面纱,这是一种能够携载核弹头的洲际弹道飞弹。
在台上发表演说时,习近平引用了毛泽东的名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他继续说道:「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
然后我发现了她。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身穿灰色粗花呢套装,站在习近平身旁。中国领导人在告诉全世界,他全力支持林郑月娥和她的警队。这种忠诚度的展示对林郑月娥来说如此重要,以至于她选择在多数香港居民预期将出现紧张情势的一天离开香港。示威者计画要反制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国庆宣传活动。阅兵游行结束后,香港居民在街上集结。数万人在购物商场和摩天大楼间游行,高呼「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在某些地区,示威者向警察投掷燃烧弹,并砸毁那些被视为与中共立场一致的店家橱窗。
在荃湾区,警察与挥舞着金属棍的年轻示威者大打出手。一名警察被推倒在地时,另一名警察背靠着停业的商店门口,拔出了枪。一名示威者朝他挥击。这名警察近距离开枪,击中这名十八岁男子的左肩。这是自六月抗议活动展开以来警方第一次射伤平民。记录下这起暴力事件的手机影片迅速流传,导致更多人谴责警方,并声称林郑月娥放任香港变成战区。这些事件仿佛一九六七年父亲前往美国前夕在香港爆发的冲突,当时英属香港警方手持警棍和催泪枪对抗左派示威者。
在习近平阅兵仪式的三天后,我在潮湿的周五早晨搭上高铁列车。这班列车疾速横越中国,停靠在长江岸边的武汉,穿越南方的丘陵和稻田,最后驶入香港。九个小时内,列车跨越了两千四百多公里。想当年,父亲的旅程需要花好几天的时间。
我拎着行李从金钟的地铁站出来时,天已经黑了。金钟位于香港岛中心,充满了高级购物商场和办公大楼。我正要穿越主要干道前往饭店时,一位年轻人在距离我九十公尺的街上朝着广告看板喷漆,然后迅速逃走。喷漆写的是一句咒骂林郑月娥的话。午夜过后,我听到饭店周围的街道上传来喊叫声。数以百计身穿黑衣、戴着口罩或头套的人刚从示威现场离开,他们经过这个地区,同时高喊着口号。
近年来,金钟一直是吸引示威者集结的地方。金钟是香港立法会的所在地。今年初夏,示威者曾闯入空无一人的立法会会议厅。在香港官员眼里,这表示抗议行动已经提升到新的层次。这些办公大楼也让金钟成为二○一四年雨伞运动的集会地点,当时的民主示威运动持续了数周之久。那年十月,我经过夏慤道上庞大的营地,采访那些担心公民自由遭北京领导人剥夺的学生。当时北京当局宣布改革香港选举制度,因而触发了这场运动。这场运动持续了数周,特定的象征符号在全球的关注下格外显眼:黄色雨伞,因为示威者曾共同撑起雨伞形成防护墙,以抵挡警察使用的催泪瓦斯;还有黄之锋,他是身型瘦弱的十八岁学生,创立了民主团体「学民思潮」(Scholarism)。但当局最终消磨了示威者的意志,拒绝回应他们的诉求,这场运动也逐渐式微。
在接下来的五年间,年轻的社运人士研究了二○一四年发生的事件以及雨伞运动中的弱点。现在,到了二○一九年,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来组织示威运动。这场运动没有明显的领导者。示威者加入Telegram上的聊天群组,透过一连串的来回讯息进行交流,针对每天的行动达成共识。在外人看来,看似是杂乱无章的声音。示威者还采用了香港武术家与电影明星李小龙的经典口号,听起来简洁而优雅:「如水聚散」(be water)。这个口号的目的是避免发生正面冲突,以免让警察占上风。如果眼看暴力冲突一触即发,示威者会冲进香港的大街小巷,进入商店、公寓大楼以及地铁站,然后在其他远离公安部队的地点重新现身。示威者不会像雨伞运动时那样建立营地,集会地点也会在最后一刻才决定。他们的目标是让示威行动变得难以预测,避免成为当局锁定的目标。
露西.江(Lucy Kong)坐在高架道路下的街道上,正在用水冲洗她小腿上的伤口,其他示威者从她身旁走过。她是在与示威者同行时摔伤的。我们在金钟,也就是靠近中环和皇后像广场的地方,皇后像广场的集结将是这次游行的高潮。露西像所有示威者一样身穿全黑服装,她还戴着黑色的Patagonia帽子和肩背小包。她在银行上班,已经受够了香港的公民自由不断受到侵害。她告诉我,在这里看到年轻的抗议者很鼓舞人心,但他们需要外部力量来协助他们抵抗共产党。 「另一种形式的冷战可能即将来临,」她说,「这是文明世界与共产世界的对抗。」
她说的文明世界是指美国。在香港的这几天里,我不断听到这句话。就在遇到露西之前,我和示威者一起走在街上,看到一个人穿着美国队长的服装,还带着盾牌。有些示威者挥舞着美国国旗或挂在木杆上的山姆大叔海报。像露西这种三十岁以上的香港居民,还记得在一九九七年亲眼目睹大英帝国将香港移交给另一个帝国,过程中英国人完全漠视香港居民的意见。但是现在,他们又将希望寄托在另一个遥远的帝国身上。露西说,他们别无选择:共产党以及中国太强大了,只有美国能够对抗他们,并替示威者捍卫他们的权益。川普是美国总统,有些示威者深信他会伸出援手。
「如果川普总统发表更多相关言论,就会制造更多压力。」露西说。
我不知道该跟她说什么。川普政府的一些官员曾经告诉我,他们担心北京可能会出动人民解放军来镇压示威活动。但很明显的是,川普本人根本不关心示威者。川普是个商人,交易和利润是他看待世界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川普希望他的手下与习近平达成贸易协议,他甚至很钦佩中国领导人能彻底掌控一个拥有十四亿人口的国家。
对美国抱有信心的示威者正关注着一项在美国国会审议的法案,即《香港人权与民主法》(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美国国会议员利用香港议题来展现他们的反中立场。这项法案一旦通过,将促使美国政府针对试图镇压示威活动的中国官员实施经济制裁与旅游禁令。但美国的政府官员本来就拥有这项权力,却迟迟没有行使。 「制裁香港官员将有所帮助,」露西说,「这会让林郑月娥三思而后行。这些官员都有亲属具备美国公民身分。」
我想到所有华盛顿当局实施制裁的国家,像是俄罗斯、伊朗和北韩,但此举似乎对这些领导人的行为没有什么影响。在露西和我交谈时,示威者开始从我们身边匆匆跑过,互相喊着要继续前进。我闻到一阵催泪瓦斯的味道。在附近的某个地方,警察正朝人群发射催泪弹。我跟着人群跑向皇后像广场。示威者很快就放慢了脚步,试图弄清楚警察在哪里。有人告诉我附近有间教堂,数十名被催泪弹击中的示威者在那里避难。接着突然下起雨来,人们在阴暗的天空下返回家中。当天的游行就此划下句点,但大家都知道这一切尚未结束。
我在脸书上收到表亲洁西(Jessie)的讯息,她从小在香港长大。洁西是南希的女儿,南希是我母亲的表亲,一九九七年我第一次来香港时和南希一起吃过点心。洁西和她的父母参加了我在北京举办的婚礼,我最后几次来香港时还和她一起喝过酒。她告诉我,现在她对自己家乡所发生的一切感到心碎,她希望国际新闻媒体的报导能对香港以及北京当局施加压力。 「这里的情况越来越糟糕,而且似乎看不到尽头,更不用说是正面的结局了。」
抗议活动就这样持续到秋天。所谓的前线社运人士与警方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在香港市中心,人群在催泪瓦斯中冒险前进的场面屡见不鲜。示威者戴着各式各样的面罩,像是外科口罩、大围巾、防毒面具以及护目镜。我也随身携带了一套防护装备。香港政府试图禁止市民在集会游行时蒙面,但示威者无视了这项命令。
十一月四日凌晨,二十二岁的大学生周梓乐从停车场的三楼坠落,四天后在医院离世。示威者表示他遭到警察追捕,但没有证据能证实这项说法。周梓乐是首位在抗议现场身亡的示威者,这让社运人士群情激愤。他的照片遍布了整座城市,人们在大学校园、街角处和公园留下字条与蜡烛追悼他。十一月的第二个周末,人们在公园举行了大型的烛光悼念仪式,纪念坠楼身亡的周梓乐。
为了重振士气,第一线的社运人士呼吁大众在下周一(十一月十一日)上街游行。他们的目标是在上班日让香港的多数地区陷入停摆,实施大规模关闭。这是示威者自八月以来首度尝试的升级策略。
周一,我搭地铁到将军澳,也就是周梓乐去世的地方。当时正值通勤高峰,人们沿着主要干道步行上班。接着,一小群年轻人开始聚集在十字路口。我看到其中两个人把蓝色脚踏车推到路口中间,然后丢在那里。这些人朝街上扔了些垃圾,并放下塑胶交通锥。司机停下车,无奈地按着喇叭。然后,一辆货车很快停了下来。六名警察跳下车,冲进十字路口,把脚踏车拖到一边,清理街道。车辆又开始继续前进。有些司机大声表示感谢。警察冲向站在人行道上的几个人,他们一直在用手机拍照和录影。 「不要打人!」一位女士喊道。
同样的情况发生了好几次,示威者将更多的脚踏车和杂物搬到十字路口,警察则快速冲过来移除这些物品。有些警察身上带着贴有萤光橘贴纸的步枪。有人警告我,这些步枪里装有海绵弹。有一次,一名警察冲向街上的一名示威者,举起手里的步枪,朝男子的背部开了一枪。站在人行道上的数十人对着警察大吼:「不要开枪!」、「你真的朝人开枪?」
办公室主任奈森.谭(Nathan Tam)在被封锁的十字路口下了车。 「我对这些示威者并不感到愤怒,」他告诉我,「我知道这是政府的错。但对于有家庭和工作的普通人来说,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我在六月时参加过游行,但结果又如何呢?如果政府不愿意听你的意见,除了移民之外你什么也做不了。现在,我非常庆幸去年就把儿子送到英国。否则,以他的个性,他现在可能正在外头抗议,还可能挨子弹。如果这里的情况变得非常糟糕,我会想办法让我的家人离开这里。」
过了一会儿,警察忍无可忍了。在我们的北边,一群警察开始向示威者发射催泪瓦斯。我看到了浓烟,也闻到了刺鼻的瓦斯味。我冲进购物中心的一楼。我周围的人都在咳嗽,商店店员拿着瓶装水冲了出来,让大家赶紧用水冲洗眼睛。
我搭上巴士和地铁前往中环,发现办公大楼、百货公司和殖民时代的政府大楼之间也上演着类似的场面。警方与示威者对峙,其中包含身穿西装、戴着口罩的上班族。发射出的催泪弹在空中画出一道道弧线,落在街道上。随着警方阵营持续推进,社运人士持续后退并逐渐散去。示威者也让这里的交通陷入瘫痪,他们用交通锥、竹竿以及砖块沿着主要干道建立了临时路障。在干诺道上方的天桥,有人悬挂了巨大的白色标语,上面印有肯塔基州共和党政治家、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Mitch McConnell)的脸孔。标语上写着「参议院该采取行动了」。这个标语强烈要求麦康奈协助通过正在院会审议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
在那之前,两部令人震惊的影片已经广为流传。其中一部影片显示,一名身穿黑衣的年轻人在人潮汹涌的十字路口走向一名警察,接着那名警察举起手枪,近距离射击示威者的胸部。在另一部影片中,一名看似支持中国政府的年长男子在行人天桥上嘲笑着示威者,后来有人朝他身上泼洒汽油,另一人则朝他扔了一根点燃的火柴。那名年长男子随即全身着火。到了傍晚,这两起暴力事件的受害者都躺在医院病床上,情况十分危急,性命垂危。情势不断地恶化。很少有社运人士希望暴力冲突演变到现在这样的程度。
我搭乘地铁回到九龙。弥敦道是香港相当热闹的商业区,也是香港重商主义的象征,人行道上总是挤满了前往珠宝店和电子商场的消费者。但现在却出奇地冷清。商店全部关门,数以百计的示威者在街上游荡,街上没有任何车辆在行驶。人们在路上放置了砖块,阻止汽车与其他车辆通行,封锁了香港极为重要的地区。在弥敦道的一个街区,六辆双层巴士被弃置在街道中央。这一幕就像末日电影中的场景,仿佛文明世界突然陷入停滞。
我闻到了橡胶燃烧的味道。隔壁街区传来的爆炸声响让我吓了一跳。我走近时,发现示威者放火烧了电线杆上的配电箱。附近有一群人将他们在别处砍下来的树干拖到马路中央。还有一些人手持长棍和砖块,正在砸中国建设银行分行的铁门,这间银行是总部设在北京的国营企业。有人大喊警察带着水炮车来了。所有人迅速散去。我从清晨就开始奔波于各个地区,突然感觉一阵筋疲力尽。我走到地铁站的入口处,准备下楼时却停下了脚步,因为我看到示威者正试图拉下铁门。他们对着地铁站大喊,说工人没有关闭地铁站是叛徒。我开始跑向下一站。我知道政府已经宣布宵禁,要求人们离开街头,警方很快就会开始搜捕滞留在街上的人。
在接下来的几天内,城市的部分地区仍然处于瘫痪状态,主要干道上堆满了障碍物。示威活动依循着固定的模式。人们会在中午时于中环举行集会,然后就地解散。但在十一月中旬的那一周,最重要的示威行动转移到大学校园。警方首次试图闯入校园,显然是为了追捕示威活动的领袖和其他知名的社运人士。到了周一,也就是全城爆发动乱的那天,警方在中环山上香港大学(简称港大)校园周边的宿舍里拘留了一名学生。当天晚上,动乱逐渐平息,但紧张情势持续升温,有消息指出在城市另一端的香港中文大学附近有几名学生被捕。也有消息传出,警察开始进入校园。在此之前,香港的校园一直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空间。学生在校园内能够感到安全,不必担心遭到报复,他们集会与发声的权利也受到保护。
香港的公立大学总共有超过八万六千名大学生和将近一万一千名研究生。由于周一爆发的动乱,市政府宣布停课一周。现在学生可以整天在街头参与示威活动,然后重新集结并制定计画,睡上几个小时,天一亮就准备再次出动。
周二,我来到香港大学。在他们的同学遭到拘留后,学生们接管了校园。我和一位二年级的学生加百列.冯(Gabriel Fung)一同走在几乎空无一人的校园。 「人们已经意识到,抗议、运动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他告诉我,「无论你身在何处,这些事情都会在某些时刻影响到你。」这里和其他学校的中国大陆学生大部分都离开了香港,至少是暂时离开。第二天,警察护送数十名学生越过边境前往深圳,深圳的饭店也为他们提供免费房间。
香港的大学各有特色。香港大学创立于一九一一年,是香港历史最悠久、最具声望的大学。香港大学在建制派人士之间占有重要地位。许多香港大学的学生都是曾经就读国际学校的外国人或香港居民,英语是他们主要的语言,其校友包含警务处处长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但政府与警方的行动却让学生变得激进。在学生遭到拘留的消息传开后不久,有人在网路上发布了影片:两位自由派法学教授傅华伶和陈文敏在校园内用英语对一群愤怒的学生发表演说,恳求他们不要诉诸于暴力。一位蒙面的女子高喊,他们别无选择。 「我们要牺牲多少人?」她问道。
「我们更好,我们和他们不同。」傅华伶说。
「但我们不会原谅他们,」一位年轻人说。 「我们不会忘记。」
周一晚间和周二早上,警方再度来到校园,试图清除路障。在学生的反抗下,他们发射了催泪瓦斯,然后撤退。校园的神圣性得以维持。我在下午抵达时,看见戴着口罩的学生守在路障前,各个小组封锁了从远处薄扶林道通往校园的不同路径。在其中一些入口处,电梯连接着校园与道路。教授和行政人员走到学生守卫身边聊天。随着夜幕降临,学生们交换轮班。
我漫步在校园的主要建筑之间。在庆祝二○一九年毕业生的室内标语上,有人漆上了「明德革命」的字样,这句标语结合了革命的精神以及学校的校训。在户外,一名蒙面的学生坐在墙边,用手机看着影片,墙上的标语写着「我反抗,故我存在」(Je me révolte, donc je suis),即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卡缪(Albert Camus)的名言。其他涂鸦就没那么高雅了,这些图画和标语指控香港警察轮奸、鸡奸和谋杀。
我走进一座中央露天庭院,抬头仰望着高耸的血橙色方尖碑。雕塑上呈现了数十具扭曲、赤裸的躯体以及变形的脸孔,纠缠在一起的尸体在尖叫声中凝结。这简直就是但丁笔下的地狱。我突然惊讶地意识我看到了什么。这座名为「国殇之柱」的雕塑是由丹麦艺术家所设计,并于一九九七年六月四日放置在维多利亚公园,当时许多香港居民都认为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为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受难者举行大型烛光晚会。二十二年后,在我凝视着那些受苦的面孔时,我的思绪又回到了那个潮湿的夜晚,当时我站在公园里凝视着同一座雕塑,人们手持点燃的蜡烛从雕塑旁经过,悼念那些在天安门广场丧生的人。
当时,这座铜像不仅象征着中国早期那段噩梦般的历史,也代表着香港居民在英国将殖民地移交给中国时的那份恐惧。多年来,这座雕塑逐渐成为国家恐怖主义以及对抗国家恐怖主义的象征。如今,在香港的山丘上,身着黑衣的蒙面学生行经这座雕塑,前往刚筑起的路障。雕塑底座上刻着「老人岂能够杀光年轻人」(The old cannot kill the young forever)的中英文字样。
周二下午,警方试图冲进通往香港中文大学校园的二号桥路障,该校区位于新界高地。这座行人天桥建于吐露港公路和东铁线之上,在全城行动的号召下,学生向下投掷砖块与其他物品,导致当地交通和火车被迫停止。
香港中文大学校园被视为整座城市示威活动最激烈的地方。许多学生积极参与夏天的示威活动,他们的学校因此被称为「暴动大学」,学生也对这个称号引以为傲。这座校园里的两万名学生大多以粤语为主要语言,许多人与父母住在拥挤的公寓大楼里。校园的位置相对偏僻,从市中心搭地铁到学校需要一小时。学生已经开始在道路的入口处建造砖墙。一些从其他地方来的示威者也加入了学生的行列。
周二,警方为了争夺行人天桥的控制权而展开攻击,导致了一整周连续的示威活动中最戏剧性的冲突。警方发射了数百枚催泪弹和橡胶子弹,学生则投掷汽油弹和砖块。超过一百名受伤的学生被送往体育馆内临时设立的急救诊所。校长段崇智一度试图与警方协商,但暴力冲突再度爆发。学生并没有退缩,警方则在逮捕了数人后被迫撤退。
到了十一月十五日星期五,学生仍占据了香港各地的五所大学,准备迎接警方即将展开的一连串攻势。就在当天,我造访了香港理工大学,看着学生在空荡的游泳池里练习投掷汽油弹和射箭。就像香港中文大学一样,香港理工大学也坐落在交通要道上。与校园相连的高架道路横跨在通往红磡海底隧道的多线道之上,而这座海底隧道可让车辆往返于九龙与香港岛之间。政府必须控制大学,才能让隧道再次恢复运作。
然后一夜之间,其他四座校园内的学生都逐渐散去了。周六破晓时,筑起的路障已遭到弃置。附近的居民与警察开始清理学生留在路上的杂物。唯一坚持下去的是理工大学,学生已准备与警方展开最后的对抗。我与这些学生交谈时,感觉到有些人渴望成为烈士。各地校园里最狂热的学生都集结在这里,准备参与最后一战。
周六晚上,警方开始试图突破外围路障。举着防暴盾牌的警察与装甲车并肩前行。他们沿着一条宽阔的大道朝学校前进,然后在接近路障时放慢了速度。学生抛掷汽油弹、朝警方射箭。周日破晓时,警方出动了他们在城市各地使用过的武器:水炮车、橡胶子弹和催泪瓦斯。学生坚守阵地,一次又一次击退警察的进攻。一名警察腿部中箭。学生领袖表示,示威者遭水炮击中后,出现眼部受伤和失温的情况。警方试图从学校后门突破防线。一辆装甲车缓缓驶向后门的路障。示威者朝装甲车投掷汽油弹,车辆陷入火海。装甲车驾驶尽速后退。在校园的那一侧,靠近红磡海底隧道的高架道路都因燃烧弹爆炸而留下焦黑的痕迹。玻璃散落一地。在北京,《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社群媒体上发布了警车着火的影片。 《环球时报》是在中国流行且与共产党有关联的民族主义媒体。 「在这种情况下,警察应该获准发射实弹以制伏暴徒。」胡锡进写道。
警方威胁将在周日晚上对示威者使用致命武力。接近午夜时,二十二岁的学生威廉.刘(William Lau)告诉我的同事:「我知道今晚警察有可能会向我们开枪,但现在我们别无选择」。他说校园内仍有约五百名示威者。在校外,一些学生的支持者试图突破警方的封锁线进入校园,却无功而返,其中包含夏志诚主教(Bishop Joseph Ha)和来自布朗克斯(Bronx)的美国牧师威廉.德夫林(William Devlin)。我在两天前进入校园时遇到了德夫林牧师。现在他在电话中告诉我,他在经历了四个小时的对峙后离开校园。他说示威者并没有被警方吓倒,他们已经做好了被逮捕的准备。香港各地的居民都从社群网路和电视新闻报导中听说了这场围城。民众从香港各地赶来,聚集在大学校园附近,试图把警察从校园引开。
香港的医院管理局表示,周日的冲突中至少有三十八人受伤。围城持续到第二天,伤亡人数增加了三倍。在一些街区,警察站在学生群体旁边,这些学生坐在人行道上,双手反绑在身后。他们在离开校园时遭拘留。泣不成声的家长在警方的封锁线外举行烛光守夜,为仍在校园内的子女求情。这些孩子试着寻找逃跑路线。有些人将绳索绑在行人天桥上,沿着绳子摇摇晃晃地移动到下方的道路,接着骑摩托车而来的同伴将他们接走。其他人则爬过下水道逃走。
仍留在校园里的一百多位示威者感到恐惧与疲惫。眼看黎明就要来临,有些人陆续离开。这一切有种即将落幕的感觉。这是香港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示威运动,在这最动荡的一周,抗争的余烬就此熄灭。在接下来的几天内,有更多的学生悄悄溜走或在离开时投降。留守的学生渐渐变得虚弱,饿得奄奄一息。警方在十一月二十八日进入校园,也就是爆发最激烈冲突的十一天后。他们发现学校里没有人。
后来的示威活动再也没有达到如此剧烈的程度。在那一周之后,只要民众在街上聚集,就会遭到警方迅速逮捕。美国政府颁布了许多香港居民所希望的惩罚性法令,但这并没有带来任何改变。香港的地方官员和北京的统治高层对此置之不理。然后香港迎来了冬天与农历新年假期。有人推测示威活动可能在过年后再次升温。但到了二月,首次在武汉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迅速蔓延全世界。世界各国纷纷在三月进入封锁状态,关闭国境。一夜之间,中国化身为与外界隔绝的庞大堡垒,香港则成为堡垒中孤立的封地。
二○二○年六月,共产党对香港施以致命一击。而早在一年前,林郑月娥推动的《逃犯条例》修订案就已经引发香港的大规模抗议。北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香港国安法》,这是比《逃犯条例》更严厉的法案。 《香港国安法》于六月三十日晚间十一点生效,比英国将香港移交给中国的二十三周年纪念日还早一小时。新的《香港国安法》赋予香港安全机构更广泛的权力,允许北京的中央政府绕过香港法院,介入所谓的国家安全案件,并直接监督具有政治性质的新国家安全机构。当然,国家安全的定义十分模糊且容易受中共操纵,当局能够以任何方式加以运用。
新法案通过后,异议分子很快就遭到拘留。今年夏天,最引人注目的案件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遭到逮捕。在将近一年后,二○二一年六月,《苹果日报》被迫关闭,使得这份香港重要的民主派报刊结束了长达二十六年的运作。隔年,黎智英因两项诈欺罪成立,遭法院判处五年九个月徒刑。
许多外国记者纷纷离开香港,因为他们担心公安部队和法院可能会用新法令对付他们。有些教授和学者也选择出走。学校老师不知道他们在课堂上还能说些什么。
二○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香港大学校方在放置「国殇之柱」的大楼周边设置了警戒线。保安人员和工人在接近午夜时抵达现场。附近的居民看到卡车,他们拍下的照片显示,工人搬出了一件裹在白色包材中的物体。第二天,学生进入这栋大楼时,他们看到曾经矗立着雕塑的中庭如今空无一物。
随着这些事件的发展,我想起了一九九七年夏天正在转变中的香港,当时是我第一次造访香港。我看到这座城市经历了日本侵略、毛泽东时期由中国大陆蔓延过来的紧张局势,以及在伦敦与北京当局达成秘密协议之后,英国政府逐渐交出香港主权的过程。我还记得在那次访问时与黎智英的会面,以及在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晚会中第一次亲眼看到「国殇之柱」。英国将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的过程看似困难重重,但也蕴含了无限可能。当时,乐观主义者认为香港有望改变中国,而非香港被迫接受中国的改变。
我也想相信香港和这座城市的无限可能。我的家族史根植于这座城市的理念之中,而香港远远不止是一座城市而已。香港曾经是各个帝国关注的焦点,但香港人民创造出自己的身分,也塑造了自己的主体性。父亲、母亲与他们的家人就是其中的创造者。香港曾经是他们和许多中国人的避风港,这些中国人在大陆的动荡不安之中寻求庇护。因此,他们把香港变成了自己的家,将他们的梦想和欲望寄托在这座城市。
目前看来,共产党似乎已经浇熄了最后一丝希望。习近平和他的同志们认为,根据他们自己的方式控制香港是让西方帝国主义时代走向终结的必要之举。虽然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已经归北京当局所控制,但某些制度和理念仍然存在。习近平试图强行将这些制度和理念连根拔起。他在上一次的镇压行动中取得了某种胜利,但他不知道革命的火苗仍在何处燃烧。
在许多中国以外的人眼中,香港变得与新疆和西藏一样,成为共产党压迫的象征,也是共产党试图建立新中华帝国下的牺牲品。北京当局透过控制边疆地区来界定国家的势力范围,这些边疆地区曾经是父亲生活及劳动的地方,也是他的家族(也就是我的家族)的祖籍地。政府的控制影响了数百万人的生活,仿佛一股巨大的平衡力量,旨在建立横跨时空的伟大帝国,确保臣民都安于其位。父亲和母亲都明白这一点。有些人对这种统治方式嗤之以鼻,有些人则欣然接受,并认为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手段。我在这片土地上许多不同的角落,透过各式各样的视角,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我看到人民认真扮演自己的角色,努力耕耘自己的土地,并尽力超越统治者对他们的期待。
在中国生活的那几年,我曾经想像有朝一日我会搬到香港,与父母亲一起走在街头,透过他们的视角以及记忆,尽情体验这座城市。我们会在城市里过上悠闲的生活。我们会逛市集,在餐厅里吃点心,然后坐电车穿越香港岛的心脏地带。他们会指给我看他们年轻时去过的地方,然后讲故事给我听。
或者我会与父亲一起飞往新疆,一同穿越草原、高原以及高山峡谷,然后他会谈起他数十年前对此地的印象。我曾有幸在他与高中同学重聚时与他一起造访广州。我希望在中国与他们共享更多的体验,因为我认为这样既能更深入了解我的家族,也能洞察中华文明的核心。
在示威活动那年离开香港后,我知道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父亲年纪大了,不适合长途飞行。他的身体与心智都变得迟缓。即便不考虑这些,这些城市、这个国家、这片土地都不复以往。一起旅行的时机已经过去了。他还有他的回忆可以分享,他的故事也还没有被人遗忘,如今这样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