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風 Matters 5 月 7 日
多数中国企业一开始就内设共产党的小组组织,即使是非中国企业在中国设立的子公司也不例外。很多大型企业的高阶主管(包括政府未掌握直接所有权的企业)都是共产党党员,理由很简单——党员的身分让他们更容易获得晋升与支持,但他们也因此不得不遵守党的纪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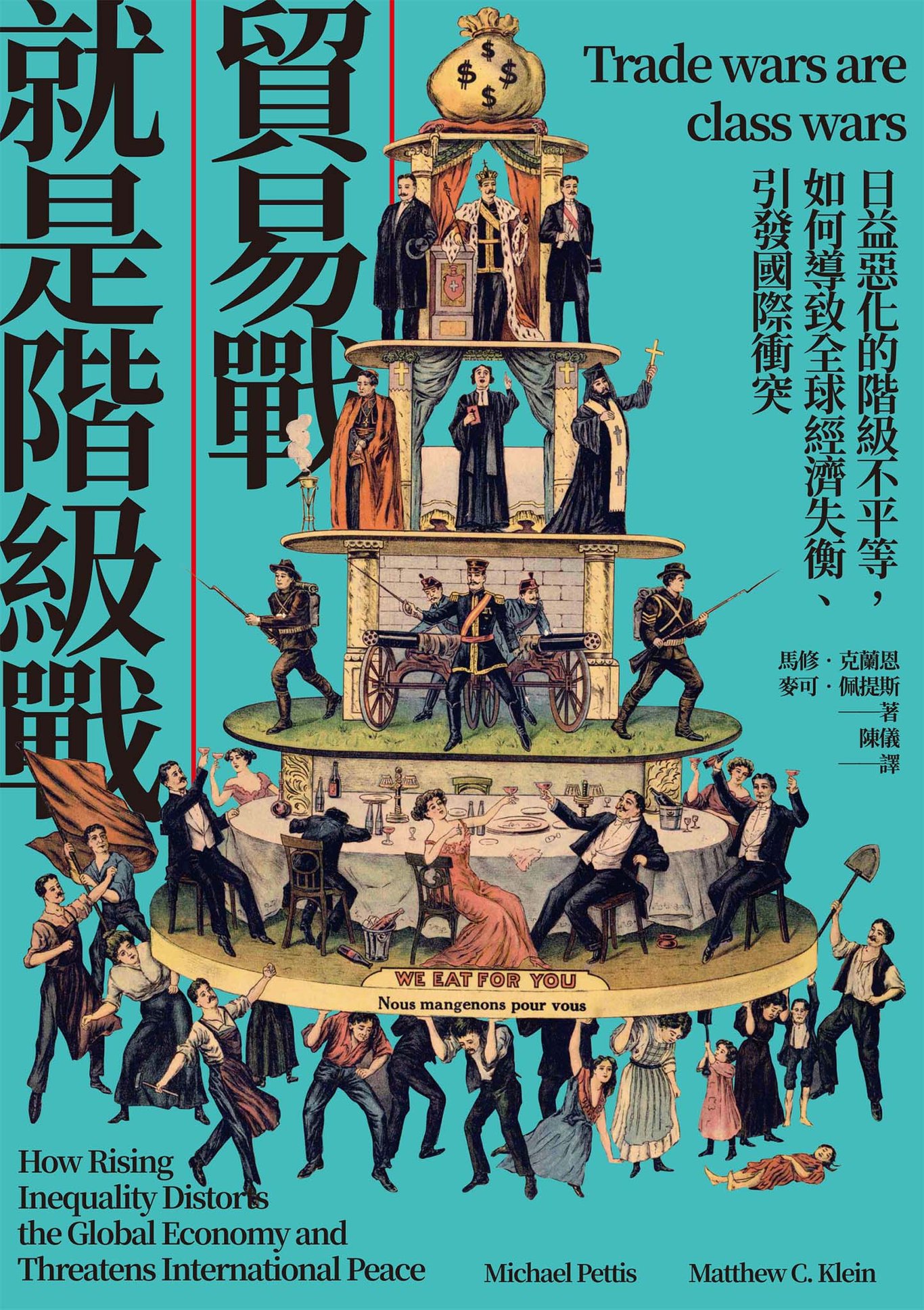
中国的失衡是否将再次震撼全世界
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它的年度经常帐顺差在二○○八年达到四千两百亿美元的高峰后便开始萎缩,到二○一九年上半年,换算成年率的中国经常帐顺差已降到大约一千九百亿美元。无论是以绝对数字或相对中国经济规模而言,中国的主要失衡之一似乎已经解决。不过,更详细检视就会发现,中国的外部再平衡进程非常脆弱,且随时有逆转的可能。劳工与退休者的财富持续遭到移转,并导致中国的消费继续受压抑。一旦投资支出减缓但家庭支出却未出现抵销性的对应增加,中国的顺差将再次扩大,这将对世界上其他经济体造成损伤。
首先要注意的是,无论是就绝对数字或相对世界上其他经济体的经济产出而言,中国的制成品贸易顺差已远比二○○八年时高。换言之,中国的超额生产所造成的过剩供给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进一步恶化,而中国的贸易伙伴吸收这些过剩供给的负担也变得更加沉重。从这个视角来看,所谓的再平衡根本没有发生。
令人意外的是,这是发生在中国制造业出口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已渐渐式微的时刻。在二○○七年至二○○八年间,中国的制造业出口大约达到GDP的三○%,但目前这个数字降到只剩一八%。这个现象的局部解释是,中国产出约当的全球产出的整体占比持续上升,所以中国贸易帐与经常帐收支的变化对中国国内经济的意义与对其他国家的意义大不相同。
然而更重要的原因和中国对进口制成品的支出变化有关。一如所有国家,中国进口制成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利用进口的零组件制成品来生产最终成品,而这些成品最后将出口到其他国家,二是进口制成品来满足国内投资与消费的需要。目前这两种进口对中国的重要性都日益降低,这导致制成品进口总额约当中国GDP的比重,从二○○四年的二三%,降至目前的一○%以下。这可局部解释为何中国二○一九年年中的整体贸易顺差看起来丝毫未受美国的关税影响。
部分原因则是中国企业不再需要为了出口最终成品而进口那么多零组件,因为中国国内的供应商渐渐有能力提供那些零组件。在二○○○年代初期,中国的先进制成品出口值有三分之二来自海外,但如今中国先进制成品的价值多数来自中国本地的劳动力与资本。如今的中国劳工早已不是单纯从事零组件组装(将别处制造的先进零件组装在一起)作业的低阶劳工。在此同时,中国的国内产能也已非常能满足国内的需要:最终制成品进口值约当中国GDP的比重,已从二○○四年的九%降至目前的五%以下。 「二○二五中国制造」的行动计画明显旨在加速这个进口替代流程。
进口替代的成功,局部是拜中国政府全面鼓励中国企业以国内生产取代外国生产的政策所赐,只不过,这使中国消费者的成本增加。中国自二○○一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就小心翼翼地信守它对WTO的承诺,并遵从WTO裁判的决定。但中国经济体系基本上可能和凡事依规定行事的贸易体系不相容,因为中国向来以党领政,这个模式使政府掌握了支配企业的巨大力量。多数中国企业一开始就内设共产党的小组组织,即使是非中国企业在中国设立的子公司也不例外。很多大型企业的高阶主管(包括政府未掌握直接所有权的企业)都是共产党党员,理由很简单——党员的身分让他们更容易获得晋升与支持,但他们也因此不得不遵守党的纪律。
即使是非党员的高阶主管,通常也会努力以北京当局的所有优先考量为重。法律学术界人士柯尔提斯.米尔豪特(Curtis J. Milhaupt)与郑文通(Wentong Zheng)「发现百大民间企业中有九十五家、十大网路公司有八家公司的创办人或实质控制者,目前或过去曾是中央或地方党政组织(如人民大会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员之一。」监理机关可就任何和那些高阶主管有关的主题要求他们接受约谈,而这样的情事也确实屡见不鲜。
中国的金融体系受国营实体支配,这让党掌握更大的奖惩力量,积极促进党的目标的企业将获得奖励,而不愿意配合党的企业则会受到惩罚。米尔豪特与郑文通提到,民间企业「在商业判断上经常受政府任意干预的影响,几乎没有自主权可言」,因为「政府对民间企业行使巨大的法外(extra-legal)控制权」。
正因如此,这个体系几乎不用关税也能将国内需求导向国内生产。政府可能经由直接命令的方式,要求企业高阶主管采用中国供应商、舍弃外国供应商。这些工具让中国政府得以进行一种现代版的李斯特国家系统,在这个「显性关税已被视为过时」的时代,那是非常合适的国家系统。这些作为的结果是:不同于其他国家,自二○○○年代中期开始,进口对中国已愈来愈不重要。
我们可轻易拿中国的制造业贸易数据和表彰其他国家实际经济活动的公告数字进行比较。但中国的整体经常帐顺差数字并不适用相同的逻辑。根据官方公告数字,中国对其他国家的旅游服务出口趋向停滞,但中国官方公告的旅游服务进口数字,却从二○一二年的一千零二十亿美元暴增到二○一八年的二千七百七十亿美元。虽然目前在海外消费的中国学生与中国游客确实比几年前多很多,但他们增加的消费远远低于官方数字所示的变化。纽约联邦准备银行经济学家在二○一九年提出的一份分析断定,中国的国际收支数据高估了实际的旅游服务贸易逆差数字,「二○一八年大约夸大了八百五十亿美元。」
这个现象最可能的解释是,很多被计为旅游的支出其实是某种形式的资金外逃。就经济意义来说,中国人到美国购买人寿保险或住宅(或将高价珠宝兑换成美元),并不等同于去度假与购买纪念品。旅游支出的遽增是发生在习近平的反贪腐运动展开之后,箇中原因不言自明。旅游支出的遽增也和中国的其他资本外逃指标有着明显的关联性,尤其是经常帐与金融帐之间的统计差异,也就是所谓的净误差与遗漏(net errors and omissions)。在二○一五年至二○一六年间,这类流出的年度金额达到七千亿美元的高峰。
中国政府以引导汇率贬值、抛售外汇准备与调整国内货币政策框架等所组成的综合对策来调和这些流出。然而事实证明,那些对策依旧不足,也因如此,中国政府在二○一六年至二○一七年间渐进式地紧缩资本汇出控制。从那时开始,很多过去特别积极以公司名义在国内贷款再转而购买海外资产的中国企业高阶主管陆续被逮捕,也有很多企业高阶主管最终在一些不寻常的情境下死于非命。
这些数据显示中国的外部再平衡进程并不像表面数字所显示的那么顺利。尽管如此,中国人对进口原物料商品的支出确实增加了,尤其是黄豆、奶制品与肉类,而且中国人确实花比较多钱在海外旅游与留学的用途。这对中国有利,也对世界有利。然而,由于中国债务过高与投资过度等所留下的遗毒甚深,所以中国到目前为止所实现的进展还是太脆弱。而且,虽然紧缩信用是中国内部再平衡的必要手段,但这最终也可能造成危害:在各种互补性改革措施还未成功达到提升家庭所得与刺激国内消费的目标以前,投资活动便已先被扼杀。若发生那样的状况,将产生国内需求遭到压抑的净影响。
那将进而产生两个选项。首先,国内生产有可能呼应国内需求的降低而减少。在那个情况下,总所得将因实质薪资减少与失业率显著上升的综合影响而降低。中国的政治系统可能承受不了那种社会动荡的冲击,就算承受得了,政府也没有兴趣冒险承担这个后果。因此,较可能的结果是国内生产降幅将低于国内需求降幅,而那意味中国的贸易顺差将因进口相对出口减少而进一步扩大。举个例子,中国政府可能选择引导人民币贬值,或寻找其他方式将这个调整所造成的负担转嫁给世界上其他地方。不管具体的机制将是什么,超额生产所造成的全球过剩供给都将恶化。从这个视角来看,中国的「中国制造二○二五」行动计画可视为一个旨在限制进口以便为即将降低的国内投资做准备的先发制人对策。
相似的,我们最好将中国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决心理解为中国为管理其内部再平衡进程的利弊得失而想出的方法,而不是旨在争夺领土或军事基地的某种谋略。还记得吗?在二○○八年之前,中国政府将购买力及商品出口给美国人和欧洲人,借此应付本国产能过剩问题。当时的中国囤积了数兆美元的美国与欧洲金融资产,换言之,它为其他国家日益增加的债务提供财源,并因此避免了国内债务持续上升的命运。然而,等到美国与欧洲的贷款人达到其举债能力上限,那个做法再也无以为继。于是,中国政府改弦易辙,转而鼓励额外的国内投资,但这个对策也不是没有代价——中国国内债务大增。诚如我们所见,事后证明这个做法一样非长久之计,也因如此,中国政府已再次改变路线。过去几年间,中国政府改弦易辙,将抑制国内信用成长与限制国内投资列为首要之务,只有少数情况例外。
因此,一带一路的真正前途在于它将创造东南亚、南亚、非洲、中东、东欧与拉丁美洲等地对中国制成品与建设服务出口的新需求。中国的银行业者将放款给外国政府,而那些外国政府将委托中国企业为它们国家兴建港口、铁道、电网、火力发电厂、电信网路等。到目前为止,一带一路确实成功创造了海外对中国企业与中国劳工的需求。不过,中国并非没有为此付出代价:中国经由一带一路,把中国国内发展模型的很多缺陷出口到世界上其他国家。中国的放款人没有对那些外国贷款人进行实地审查的积极诱因,因此,接受一带一路的国家已对中国的银行业者造成巨额的呆帐。另外,中国企业向来对它们的专案所造成的环保冲击漠不关心。迟钝的政治与文化敏感度已导致中国企业和东道国之间发生许多摩擦。即使那些问题都能一一克服,一带一路国家的整体潜在市场(addressable market)也远比北美和欧洲小。因此,中国妄想利用一带一路来取代它失去的传统出口市场(译注:北美与欧洲)的如意算盘,实在不切实际到令人难以想像。
这一切的一切都会显著牵动中国经济受当前贸易战影响的程度。只要中国还拥有举债能力,且中国政府愿意使用这个能力,那么,不管贸易战的战况有多么险恶,中国对外公告的GDP成长率,这个用来衡量经济活动,但不考虑这些经济活动是否能增加财富的指标,就不会受贸易战影响。然而,只要中国人无法自由进入出口市场,中国经济的永续成长能力将受到影响,因为一旦如此,政府将可能为了因应这个问题而盲目鼓励增加借贷,以支应愈来愈没有效益的投资活动或是家庭债务所需的资金。这虽会使中国表面上对出口的依赖度降低,实际上却会使中国经济变得更容易受贸易战伤害。截至目前为止,中国回应美国关税的方式是提高它的进口替代、引导人民币贬值以及(温和)加速国内信用成长,其中包括家庭债务。
中国需要改革一事,已在当地凝聚了相当广泛的共识,二○一三年十月的中国共产党三中全会就提供了至少部分的改革蓝图。中国已在很多领域创造了重要的进展,包括利率自由化、环境保护、医疗保险,以及一胎化政策。家庭消费相对总生产甚至也开始上升,只不过,家庭消费约当中国经济产出的占比,还是远低于二○○○年代初期的水准。下一个重要的步骤将是如何把巨额的财富与所得,从权贵阶级(尤其是中国省级与地方政府以及众多国营实体)手中。移转给家庭。这意味中国必须进行土地改革、户口制度改革、租税改革、民营化、工会合法化以及其他对策,好让家庭所得在GDP成长率大幅降低之际继续快速成长。
此时此刻,有关中国的失衡,唯一的安全预测是:未来十年或二十年,中国的失衡将会被逆转,那意味未来家庭所得的成长速度将大幅超越GDP成长。不过,这个结果可透过很多管道发生。渐进式的财富移转将使中国人的生活水准在投资活动成长趋近于零或什至转为负成长的情况下继续维持快速成长。未来中国家庭的所得与消费可能会达到每年五至六%的亮丽成长,而平均GDP成长率则将趋缓为三至四%。
重点是,不管采用什么方法,中国一定会再平衡它的经济体系——所谓物极必反,所有的失衡最终都会自我逆转。但具体的再平衡途径将取决于政治体系如何与几个无法并存的约束条件周旋。随着中国的经济继续趋缓,北京中央政府将必须和中国各个不同权贵团体建立一种全新的关系。中国将会打造一些新机构来决定这个世纪后续时间的中国经济本质。那个新关系与这些新机构将以什么面貌出现,但凭个人猜想。最好的结果是权贵分子的所得被移转给一般家庭:这个再平衡作业基本上应该能使中国不再那么需要强迫世界其他地方来填补它不足的国内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