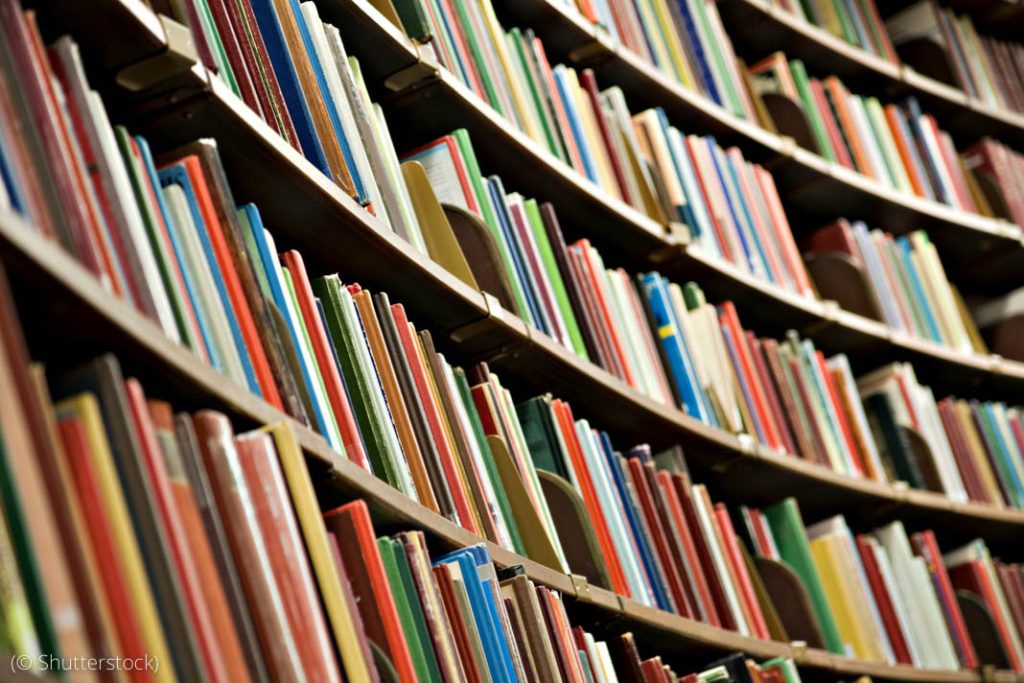作者:庄晓斌
看到独立中文笔会马建会长的一篇长文,起念撰写了这篇文章。当然这不是附庸风雅,而是由心于衷地发表感慨!我丝毫不怀疑,马建的文章和我的议论,或恐都是可以载世的文字,因为现代数字化技术的存在,我相信1000年以后人类也能历史资料库里,通过记录的文档窥视到公元20世纪汉语文化圈里各等文人的生存状态。
当然如果从这一点上解析,说我蹭了马健先生的光环,也算是恰如其分。因为我在那篇质疑曹长青先生的文章里就写过:“我的文章从来是没有文采的,就像月亮折射太阳的光芒一样,只能依靠别人的光芒,才能让自己的文字有一点点的“亮光”。
首先我就剽窃已经被中华民族捧上神坛那块“腊肉”的知识产权吧!这篇文字的副标题也可是:“二十世纪汉语文坛各类写作者阶级分析”。
我之所以在古稀之年还要给这个世界留下这一篇文字,这就像我曾说过的:“70余年的惨淡人生,早已将人情世故、世态炎凉,阅尽看饱。以前我一直告诫别人,要知道敬畏,懂得谦卑。可今天的我不敬畏,也不谦卑了,我要把久久积郁在心底里的一腔怨愤都倾吐出来,给这姹紫嫣红的大千世界,留下一段“发自肺腑的心灵独白!”
一位至今依然生存在中国大陆的作家朋友曾经这样问我:“我们热爱文学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要用一颗敏感又脆弱的心灵去跟强大的世俗社会碰撞。我们搞文学是在做什么呢?是一方面要细细梳理自己那静如深潭的情思(丝),努力编织出雨后彩虹样的倾诉;另一方面,又要遨游于众灵魂中间去寻寻觅觅那些幽微世界里的能延续人类长河的金子般的热情,同时还要汲取并激扬更可贵的——对主流文化的叛逆精神——缺失了此种精神,作家所有的作为将是一堆“沙型”。
作家的人生状态,该是自由、温情、宽容的,但又须执著和桀骜不驯。作家既要坚守丰腴的自我天地,又须向社会向人生真诚地绽放心灵,遂求永恒。——这,便是我体悟到的作家的“内质”。”
20多年前,我就说过一句堪称经典的话:“文学艺术的价值在于创作,而文学艺术的生命则在于真实。”这句话是我的秘诀。当然,我说的真实并不是指我们确凿看见的事实,而是艺术上的真实。姹紫嫣红的大千世界令人眼花缭乱,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生活也太色彩斑斓了,现实中有作家们信手可得汲取不尽的文学素材,有数也数不清的张三、李四、刘五、赵六,只要把这各色人等都揉搓成肉末并吃到自己的肚子里,才能消化成哺育自己成长强壮的养分,如此你就成功一半了。“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句话虽曾被奉为左翼文学的创作理论,但我至今仍奉为经典,这句话是一点都没有说错的。娴熟作者的生花妙笔,就是能把假的虚构的人和事写成真的,并让读者们相信这都是真实发生的事,这就是这个世界里确凿存在的血淋淋的现实!
前两天和一位远在美国的朋友通话,她向我探讨关于文学创作的秘诀。我对她说:“这其间其实没有什么秘诀,就是把张三、李四、刘五、赵六都碾碎成泥,然后再喷上自己的口水,(因和我通话的是女性,我不好把撒尿说出口)揉搓成型,再捏和成泥人,这就大功告成了。”
几天以前,在网络上搜索,竟然将十五年我在加拿大中文国际出版社出版新书时的一篇感言又翻腾出来了,因此把这篇文字也记录在这里留存于世吧!
“承蒙位于加拿大魁北克的中文国际出版社慧眼识珠,凝聚着我毕生心血的苦难之作《赤裸人生》终于可以完整地面世了。值此血泪之作首发之际,年近花甲的我禁不住老泪纵横……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今天涕泪交加,倒不是因为伤心过甚,而是感触颇深。就像一个十月怀胎的孕妇,凝望着自己历经生死劫难才痛苦地分娩出的苦难胎儿,此刻的幸福感是甚于那撕心裂肺的阵痛的。
一个普通胎儿,大约只要经过十月怀胎,就可以成熟分娩了。谁曾料想,我的这个胎儿却历遭了30多年的苦难,才拱破羊水,将完整的形体呈现在姹紫嫣红的大千世界上。
在这个繁杂的世界上,文学的天职就是真实地记录、诠释人生。多少年来,数不胜数的优秀作家创作出了无数部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我的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够有幸问世,以飨欣赏它的读者,所倚重的是:这是一部真正在监狱里写作的、表现囚徒最真实的生存状态的苦难之作。
当年构思这部作品时,我还是个顶着无期徒刑枉判的反革命囚犯。 身着赭衣的我,在那暗无天日的牢房里,用牙齿做铅笔刀书写这部血泪之作时,绝对想不到,这部作品有一天能够堂而皇之地登上神圣的文学殿堂。那时,我只是用一种近乎垂死挣扎的本能来抒发自己对人生的感悟,记录下自己在生命完结之前感同身受的这个残酷的人世,为自己也是为和自己有着相同命运的整整一代人,发出一句声嘶力竭的呐喊!
可以试想,一颗稚嫩的文学胚芽,植根在只有铁和血的严酷土壤上,这无异于把一粒种子楔入硬邦邦的石板上, 要想存活,到哪里去汲取可供自己成长的水、养分和阳光呢?然而,既然是一个生命体,它就要顽强地钻出头角,去接受阳光就不仅仅是他的本能,而且是它赖以存活的唯一选择。面对铁窗、铁门、铁镣,只有吮吸着冷的铁和热的血的养分,它才能顽强地存活,顽强地成长,能活着本身就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奇迹!
世界上,大多数文章是用墨水写的,但也有些文章是用血泪写的。倘若读者们能够感觉到这部作品是沉甸甸的,这就是血写的文字当然比墨写的文字更沉重的缘故。我不是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作家,但我肯定是这个世界上最苦难的作家之一。苦难是我得天独厚的生存土壤,也是上苍赏赐给我的一笔最丰硕的财富。从这个意义上来解析,我的文学情结就不仅仅积郁在心,而且早已经融化在我的血液中,铭刻在我的灵魂里。文学就不仅仅是我钟爱的职业,它就是我的生命!我就是为文学而生的!
多年前大陆文坛一位文学同仁曾褒奖我“像是一面寒素的旗帜,张扬着生命体的不屈,而这是任何天火也毁灭不了的。”正是这任何天火也毁灭不了的生命体,成就了我这个囚犯作家,成就了这部浸透了血泪的《赤裸人生》。
30年前,我曾经在手稿的后记里写过这样一段话:“母亲痛苦地分娩,除给了我们鲜活的生命之外,也产下了许多脏东西。鲜活的生命蓬勃向上,而脏东西是要扔到垃圾桶里去的。在我们抚摸着已经结了痂的伤口,强抑着寒心彻骨的痛楚去回首往事的时候,难道还有意趣到垃圾桶里去拣破烂么?”
“这部小说毫不忌讳地把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发生在中国大陆上的那场浩劫的惨烈、冷酷和丑陋都彰显无遗,其立意是最客观地出反映那个时代各色人等最真实的生存状态,并没有鞭尸的歹毒和快意。”
我也曾这样写过:“一个人已经死了,再用笔去鞭挞他的灵魂,这似乎无异于森阴的阎王殿里的那种声嘶力竭的拷问。揭露丑恶只是为了净化灵魂,我斗胆执笔作鞭,拷问的不仅仅是世俗百态所包蕴的灵魂,真真切切地也是在鞭笞自己的灵魂!”
发生在中国大陆上的那场“十年浩劫”已经过去几十年了。我们的民族经过了血与火的洗礼之后,已经从满目创痍的废墟上苏醒过来,个人的恩怨荣辱是不值得耿耿于怀的。我衷心地希望,我和所有欣赏这部小说的读者们,都能用博大的心胸去洞察历史,去放眼未来。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骨肉同胞的幸福安康,才是最值得牵挂的。但愿像“十年浩劫”这样的民族灾难永远不再发生!”
2010年3月于法国沙隆
上面的文字就是我十五年前的感言,今天我看到上面的文字,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今天的我依然要用一颗敏感又脆弱的心灵去跟强大的世俗社会碰撞。即便就是碰得头破血流,我亦无怨无悔!因为我终于声嘶力竭地呐喊出积郁在心头已久的话语!
公元二十世纪的汉语文坛究竟是什么样貌?马建会长的文章里似乎已经做了鞭辟入里的剖析。他是正宗中文系科班出身。做文学评论应该是他的强项。在此我也就不用再狗尾续貂了。我在这篇文章里所表述的都是我个人的真实感悟;也可以说是我发自肺腑的声嘶力竭的呐喊!
我要告诉未来人类, 公元二十世纪的汉语文坛,几乎就是一个魑魅魍魉横行的坟场,从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到现在大约整整有100年时间了,这100年间,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文化的普及使方块字儿不再只是士大夫阶层的专用工具,而成为广大底层民众喜闻乐见的交流形式。这当然该算是时代进步。但真正的话语权却从来就没有属于过底层民众。有人说:“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悲哀的民族”。但拥有文化的民族却把文化当成了给庶民们的洗脑工具。这实在是更悲哀的事情!
无情现实就是这样,近百年来,特别是中共获得统治权的七十多年来,中国大陆的汉语文坛就似如是一座死气沉沉的坟场,毫无生气可言。几乎连汪汪犬吠,都是一个腔调,这难道不是事实么?这个结论。绝对是恰如其分!
据说中国大陆汉语文坛最高端的文学奖即“茅盾文学奖”至今已评选过20几届了,中国大陆的作家几乎都以获得此奖项为荣。甚至有的作家为了获得这个奖项,不惜拉关系,花重金找知名评论家相互吹捧,更有已经成名的作家也不得不屈从上峰旨意,违心地修改自己完整作品,才能获得此项桂冠。(诸如陈忠实)然而,“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生命力究竟能有多久?能不能经得起文化市场和广大读者们的检验,这就另当别论了。
中国著名诗人臧克家曾写过一句诗:“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把名字刻入石头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
在公元二十世纪的汉语文坛,几乎所有体制内作家们都把那个最高端的“茅盾文学奖”当作那块可以“永垂不朽”的石头;但在我看来,那块石头就是耻辱柱上的墓志铭!这多如“过江之鲫”的获奖者。恐怕只能是名字比尸体烂得更早!不要说在多少年以后了,就是在现在,究竟能有多少读者还有意趣去阅读所谓的获奖作品?这难道不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吗?
当然,我如此断言,并不是否定这些作家们的才华,在这一点上我和马建会长的剖析是有歧义的。体制内诸多作家。并非都是平庸之辈。在他们之间,很多人都才华横溢。只不过是因为体制压抑,限制了他们才华的发挥,在这一点上,我坚持我以前评价丛维熙和张贤亮两位大家的观点,我的评价是这样说的:“他们不乏才华,但多年的牢狱生涯,几乎已经压垮了他们脊梁,侥幸得到恩赐。又回归到体制内,有了话语权,又可以写小说了。他们怎么敢把那黑暗龌龊地界里不堪入目的样貌,用笔展现出来呢?他们所能揭示的只是冰山一角儿,只是监狱这个黑暗龌龊地界的一点皮毛,这还是当权者容忍他们展示的那一点点皮毛,也就是肚脐眼儿下的那一点皮毛……”
我用如此轻蔑口气调侃,足可见我对文坛大家的不屑,这也是我对主流文化的叛逆,当然我还说过更狂悖的言论,诸如我曾写过:“作家像什么?作家最像妓女,两者的区别就是作家卖文,妓女卖肉,为了赚银子,他们不得不向嫖客(权贵)献媚。甚至可以说,没有良知的作家比站街女更下流无耻 ,因为站街女出卖的仅仅是父母赐予自己的肉身,而无良作家出卖的则是自己的灵魂!”“至于记者嘛,记者就是小偷,小偷觊觎的仅是游客的钱包,而记者觊觎的则是名人的隐私!两者就是这样细微的差别。”
坦诚地告诉大家,上述作家和记者这两种职业都曾是我的谋生的饭碗,因此一点不假,这两种下作的“脏活”我都干过。
在二十世纪初的武汉,一碗热干面的价格仅一元人民币,而我所供职的杂志社稿酬却是千字千元。这就意味着我那时只要在键盘上多敲打出一个标点,一顿早餐就有了。说实话,故意拉长文章的猫腻,我是真没少干过的,以至于现今写文章常常不经意就废话太多的文风,可能就是这贪婪的坏毛病所惯成的。
那么,文学的真谛究竟是什么呢?梁启超说文学是“国之魂”,而中国仅有的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之一莫言也说:“文学的主旨是揭露而不是歌颂”, 其实文学是“国之魂”也好。“是刺向我们民族心灵的揭露利刃”也罢,都是作为国学家的梁启超和身为小说家的莫言的自家之言,也都是他们独特的心灵感悟。
而西方一位文学理论大师给文学的定义恰恰如此,他认为:“文学就是一个作家用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字在和这个世界进行的独特对话。这两个独特性就是文学的特质”。我也可用更直白的语言来表述:“文学其实就是一门造假的艺术!”
世界上真正的文学大师,都是能够造假成真的巨匠。将人世间子乌虚有的事情,用一支生花妙笔编撰成可读故事,讲述给人听,并且让读者相信,这就是真实社会中发生过的事情,这也是文学艺术的一个特质。
在历史角度上求证,明清之前小说为什么不受主流文化待见,则就是因为它具有通俗可读又兼有虚假成分这个艺术特质。认为这就是街头巷议的市井虚言,只能当做可愉悦身心的故事和笑话听听而已,完全当不得真话听当成事实信的。教化人心,修补道德堤防,当然是要儒家正统的四书五经和由这些理论演绎出来的诗词歌赋和八股文类的主流文化了。这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延续承传了数千年的历史脉络。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写小说应该是老于世故的那些作家们的专利。年轻的作家们即便是才华横溢,也是决然写不出足可震撼人心,荡气回肠的小说的。50岁之前挚爱文学的中青年作家们。你们可以去写写诗歌或做些文采飞扬的美文。诗歌需要的是激情,这才是年轻文人们的专利、而美文是格调,考究的是意境和文字功底。这些通过努力专研都可悟到。而写小说就不同了,没有深厚的生活底蕴,任何天才作家也领悟不到写小说的精髓和诀窍的。只有将数十年的人世沧桑,世态炎凉阅尽看饱,才会写出那些沉甸甸的故事,才能够锥痛人心,把人类心灵深处的那相对柔软的部位捅出个窟窿来的,让灼热的血浆汩汩地流淌出来,才能收获到臆想得到的艺术效果的。
这一个创作过程,恰恰如陈粮酿酒。就是如同我的好友大陆作家羽之野先生写的那样:“作家是一帮奇异的“食毒”动物,能茹纳生活里有毒的和无毒的东西,更喜欢吞嚥那些极能“损害”人的“痛苦”——这一人的灵魂的极重要的情愫。 我这样说作家,并无戏谑之意。我是说一个作家要想写出哪怕一星半点儿能邃入读者心灵的作品,除了悟性便是“体验”。由此,作家的痛苦还算得一种“苦”吗?她已经如粮食变成酒,把本属独有的刻骨铭心的痛苦,变成了作品——献给读者,交付岁月,使其公有。这样,当这最终成了“财富”的痛苦一旦被送到书商书贩那里,又被品头论足的时候,这苦——还好意思在人前称“苦”吗?
陈粮酿酒,需要时间发酵。而沉淀发酵的时间愈久,酒味才能更香醇。为什么法国波尔多酒庄里的百年拉菲会价值昂贵,就是这个道理。我说文学其实就是一门造假的艺术,这是由衷之言。但造假也不是没有规矩的造假,仿真高手都知道的,要伪迹能够乱真,你就要绞尽脑汁去临摹真迹,如此才能蒙蔽世人眼目。而如果你的仿真和真迹一点都不像,那你就失败了。一贯造谣的骗子们也深谙此理,谣言里只有掺杂些真话,才会使人相信,这样造谣就成功了
文学是什么?文学是一个民族的魂灵,真正文学家、作家也就该是这个民族的良心。良知是不可或缺的,没有良知的文学家、作家迟早会沦落成御用的造假高手的。
马建会长直言不讳地点评了当代汉语文坛多位载誉霏霏的作家,对马建的直言不讳,我由衷地感到钦佩。在当今之世汉语文坛,终于可见一篇有思想深度的评论文章了。我的这篇文章既然是在马建先生文章的启迪之下才动笔撰著的,那么也就来个“东施效颦”,作以类同的表述吧!马建为当代汉语文坛的文学艺术划分了三大类别,我也如法炮制:但我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解析二十世纪汉语文坛样貌的。
A类,天花板级别的作家,此类作家用著作等身来形容,是远远不够的,他们作品的发行量和稿酬收入,都是天文数字。 即便是在世界范围里做比较。也恐怕是只有那部叫“圣经”的出版物是超过了他的。在公元二十世纪的汉语文坛,这样天花板级别的作家只有两位。一位是那个具有诗人气质的“腊肉”,不管他那多如鹅毛的著作是叫:选集、语录、还是诗词,反正都是天花板级别的读物,在中国大陆,曾经几乎是人手一册,人人必读,而且还要把这类经典当成教义,鼓吹为“最高指示”;我当然不会知道这“最高指示”和过去帝王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有什么实质区别?但我知道,这位天花板级作家的作品,很多都是由他的秘书代笔写的。可是他似乎也非常享受,不但冒领了大批稿费。还时常把这些稿费当做“体己银子”,赏赐给自己的亲戚和家属。当然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用稿费的名义给奴才们打赏,不是更能彰显圣君的清廉么!
公元二十世纪的汉语文坛,天花板级别的作家当然也不能就属“腊肉”一人!我要例举的例子当然还有“一尊”,这位天花板级别的作家的风格当然不同于“腊肉”,他可是能扛200斤麦子走十里山路都不换肩的大力士,背起书名来堪比相声演员的惯口“报菜名”。但却常常错别字连篇,像“通商宽衣”“精湛(sen)”,诸如此类的笑话常常脱口而出。而“一尊”却丝毫也不会觉得脸红。据说他是在位期间出版自己文集最多的中共党魁,而他那套“治国理政”理论,当然也和“腊肉思想”一样,成为了威权统治的教科书,唯一有区别的是我没有考究到“一尊”获得的天价稿酬,都赏赐给了什么人?
B类:体制内的作家:在前不久,我与在当今文坛备受赞誉的著名作家土家野夫,商榷《文学与自由》的文章里,我这样写过:“我不站队,也不预设立场。只是想表达自己的识见,说句心里话。我对大名鼎鼎的诗人韩冬也毫无敬畏之心,他的颐指气使,确实令人难以接受。这也许就是体制惯的,我揣测假如“寒冬没有貂皮裹暖,这个冬天你能怎么过?我当然也不知没有体制发给这些大作家们的足可脑满肠肥的丰腴工资和补贴。他们就凭自己一支笔还能不能养家糊口?”
这句话代表了我对体制内作家们的基本立场:我和马建会长略有歧义的是:我幷不否认体制内作家们很多都是才华横溢的大家,如果仅仅讨论学识和创作技巧。我自愧不如。但论及对文学的挚爱和作家的品格,我似乎还应该有一点点自信。因为假如这些才华横溢的大作家们都能挺直脊梁,又何愁汉语文坛不百花齐放?遗憾的是,我企盼的中华民族文艺复兴局面,并没有在神州大地上出现,这恐怕就是我此生最大的遗憾了。
C类:体制外的写作者 马建会长对这类文学现象有一段幽默的论述:“中國作家仍然要面對著社會政治的現實。做人的道德感和作品的風格是互相存在的。以消化和排泄為例來看:在中國說創作自由,是叫你隨便吃,但拉屎要由領導審查批准。中國作家只好在吃的時候,每一口都在考慮出版時能否順利通過。作品明顯地知道自己在刻意做了什么。在台灣和香港可以是完全自由的吃,更可以自己決定何時進廁所。但他們吃和拉的速度太快了點。這種現象全世界都存在著:网络文學、卡通文學等將成為主流,有独立思想的文学将被移出哲学领域,文学也将快餐化了。”
我认为马建的比喻相当形象。在20世纪,信息化,数字化技术已高速发展。“计算机能够改变历史”就是最好的诠释。在过去时代,文人们的格言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现在就不一样了。我曾经这样表述过:“凭借现代高科技的发展,现代作家们理应获得比前贤们更杰出的成就,因为鼠标一点,依托的何止是万卷诗书,而身后面依托的简直就是一座大不列颠博物馆。”有如此高科技的加持,现代汉语作家们如果还超越不了曹雪芹、罗贯中,那就只能怪自己的懒惰了。确实现在高科技数字化时代已经来临,人工智能技术也已经发展到可以替代作家从事规范写作的高度。马建说的一点都不错:“网络文學、卡通文學等將成為主流,有独立思想的文学将被移出哲学领域,文学也将快餐化了。”这就是残忍的现实,也许只有这一类的写作者。才无愧于“作家”这顶桂冠!
泛泛地议论了公元二十世纪的汉语文坛的诸多奇怪样貌,也终于轮到该议论一下我自己了。我头顶着一顶“囚犯作家”桂冠?,究竟该算是哪门子作家?
今天我就不揣丑陋,敞开心菲,也真诚地评价自己对文学艺术的钟情和挚爱!在公元二十世纪的汉语文坛里,我以为我是独占了如下的几个第一:
我是第一个曾经用“密码写作”的作家,还是第一个混迹在街头小商贩的行列里“自作自售”的作家。也是一生挚爱文学艺术,但此生可以称作为”文学艺术”的作品,却全都是自己赔钱才得以出版面世的。国内国外都是如此。至今在国内的旧书市场里,有天南地北的几十家网店在售卖自己的“文学”作品,正版,盗版的全有,可却都是“非法出版物”被人们称唤叫“作家”也有几十年了。但从来就不识得“版税”是何物?说过很多关于作家的经典语录。诸如“作家和婊子”、“作家卖书、农民卖菜都是出卖自己的劳动,这天经地义!”
我挚爱文学艺术七十年,却没有获得一丝一毫值得夸耀的业绩,现代汉语文坛,在介绍某位大家的维基百科里都是如数家珍样地罗列都得获过哪些文学奖项,而我在这个方面恰恰就是短板,此生几乎和所有的文学奖绝缘,唯一获得过的一次文学奖竟是身着赭衣时获得的“劳改文学创作一等奖”,而奖品就更奇葩了,是用十二种颜色布料拼凑成的一件劳改裤衩,这物件也成了我第二部长篇小说《老面兜》里的一个情节。议论至此,应该叫读者们了解一下我之所以能成为作家的经历了。在此我就把我之所以阴差阳错地成为了“囚犯作家”的传奇经历再赘述一遍。
当年我构思《赤裸人生》这部小说时,我还是个顶着无期徒刑枉判的反革命囚犯。 身着赭衣的我,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用牙齿做铅笔刀书写这部血泪之作时,绝对想不到,这部作品有一天能够堂而皇之地登上神圣的文学殿堂。那时,我只是用一种近乎垂死挣扎的本能来抒发自己对这惨淡人生的感悟,记录下自己在生命完结之前感同身受的这个残酷的人世,为自己也是为和自己有着相同命运的整整一代人,发出一句声嘶力竭的呐喊!
世界上,大多数文章是用墨水写的,但也有些文章是用血泪写的。倘若读者们能够感觉到我的这部小说是沉甸甸的,这就是血写的文字当然比墨写的文字更厚重的缘故。我还是要重申:我不是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作家,但我肯定是这个世界上最苦难的作家之一。苦难是我得天独厚的生存土壤,也是上苍赏赐给我的一笔最丰硕的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解析,我的文学情结就不仅仅积郁在心,而且早已经融化在我的血液中,铭刻在我的灵魂里。文学就不仅仅是我钟爱的职业,它就是我的生命!我就是为文学而生的!”
今天,我就是要用明明白白的语言,告诉读者们,我的这个苦难胎儿是如何孕育,又如何在只有冷的铁和热的血的土壤上,顽强地钻出头角,而成为一个鲜活生命的全部过程。这其间的艰难和心酸,实在是令人难于想象。以至于今天我将已经结了痂的伤疤再撕裂开来给人看,依然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楚痛……
我最初起念书写这部小说时,我还是押在中国大陆黑龙江省铁力看守所一间昏暗牢房里的囚犯,而且是刚刚越狱未遂被抓回来的未决囚犯。我被追捕回来之后,就被戴上了死刑镣,押解到更森严的铁力县看守所关押。我那时还不知道自己今后的命运会是如何?当时只是怀着一颗不甘如此就告辞人生的挣命心理,起念想把自己对这惨淡人生的感悟都用文字记录下来。恰好,一个可以外出劳动的同监犯带回来一截铅笔,就这样,我用两个窝头做代价 ,从同监犯手里换来了这一截铅笔。开始了我认为可以延续自己生命的写作。我是个政治犯,当然识得其间的风险 。因此我的写作只能以练字的借口施行、我创作出了一种密码式的写作形式 ,即把一个字 写在中间,而后就都按一定辐射序列排列。除了知道排列密码,否则随便什么人看到 ,也都是念不成句的一个个单一的汉字。我就是用这样的创作形式开始为这部血泪之作制作雏形的。
当然,写作用纸就是看守所每个月发给犯人用来揩屁股的那几张草纸了。没有纸揩屁股。我只好掏空被子里的棉絮。铅笔磨秃没有刀具修剪,只能用牙齿一点点啃掉木屑。这就是我说过的用牙齿做铅笔刀的来历。而《赤裸人生》这个书名。则是在数九寒冬的冰天雪地里,被毫无人性的武警兵将赤身裸体的我用一口大铁锅扣在了雪地上半个多小时后才悟到的。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在一次清查监号时,武警发现了我写的那些字纸,便来追问这上面写的都是什么?我一口咬定就是练字,没有什么意思,武警不信才把赤身裸体的我用一口大铁锅扣在了雪地上半个多小时后才送回牢房的。那次我被冻得几乎是脱掉了一层皮。
后来我被判无期徒刑投入到监狱,写作条件和环境相对要好多了。而我在监狱里的一切钻营,其实都是在为自己的写作创作条件。包括我积极靠近政府,也写了狱歌和表现改造题材的话剧、相声、二人转等等正能量作品。其实都是为了自己能顺利地完成这部作品不得不做出的妥协。那时的我,心无旁骛。只是想此生能把这部书写完写好。因为我犯的就是反对共产党的大罪,根本就想不到 在共产党还执政的时候,能够给我这个货真价实的阶级异己分子平反的。直到1984年春节前夕,我已经完成了《赤裸人生》的第三次修改,才在一次全监的犯人奖励大会上听到了当时兼任黑龙江省劳改局政治部副主任的曲艺家黄枫在大会上对全监犯人们讲的一句话:“全体犯人们。我代表你们的家长,你们的亲人,看望你们来了!”而备受感动。。会后我才悄悄地给黄枫写了一封信,委托就业工人在监外替我寄到哈市。
在信中,我向黄枫老人介绍了我写作此书的艰难,希望他能帮助我,使这部作品得见天日。就这样在1984年春节过后的正月初五。黄枫的大儿子(那时笑星黄宏还未成名,后来出版此书的湖南书商为了蹭黄宏的热度,称作是黄宏)代父来到革志监狱,找到我大队的朱大伟教导员,取走了《赤裸人生》手稿。后来黄枫老人在阅读完我手稿后,亲自来监狱看望我,并鼓励我先为自己申诉。黄枫老人说:“有价值的文字即使放上十年二十年后再发表,依然有价值。你只有先获得自由,有了公民权,你的作品才能有得见天日的机会。”
就这样,我在黄枫老人的鼓励下,才开始申诉,以后又先后写了数百封申诉信 ,又历时数年,在一次次被驳回后,才在1989年末得到平反获释。此书后来的出版过程也异常曲折,在此文中就不再赘述。一九九八年夏天,我在北京街头摆地摊兜售自己的苦难之作时,曾写过:“我不是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作家,但我肯定是这个世界上最艰难的作家!”当年,我曾收到过上千封来自大陆各地的读者来信,虽然这上千封珍贵来信,都遗留在大陆,恐怕今生也再难回到我的手里了。但正是那无数善良读者们的鼓励,才支持我能步履蹒跚地走到今天。
而今,20余年悠悠岁月消逝了,我已经在曾赞誉过我的读者们的视野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我的文学情结还是在我这颗不甘死寂的心灵里郁积着。这情结就像一座积聚着炙热岩浆的火山,让我惶惶不可终日。我的文学梦已经碎了么?没有!我期待着有一天,文学能成为我的情人,我可以挽着她的手,在春暖花开的原野上徜徉,把灵魂的思考诉说给未来,诉说给大地和阳光……
不记得是那位哲人说过这样的话了:“没有文化的民族是蒙昧和悲哀的民族。”但有了文化,却把文化当成某些时代宠儿们专利的民族何尝又不是蒙昧和悲哀的民族。在现实商品社会里,垄断是获取丰厚利润的最好手段。所以,某些有垄断地位的精英就把文学也当成了自己的自留地。为了自己能在有生之年获取暴利而活得滋润,就不顾社会责任而在自己的自留地上种植鸦片以牟取高利润。于是,对话语权的垄断就是这些精神鸦片制造商的一个得天独厚的法宝了。
在这样的环境中,真正鲜活的、有生命力的,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是不可能诞生的。面对这样的社会环境,有品格的作家,也只好放弃文学写作,因为你不想做毒贩子,你在自留地里就没有耕耘的权利。想说话就只有唱赞歌,离经叛道者格杀无论,手无缚鸡之力的谦谦文人,又何尝敢用生命去做赌呢?
我在一篇文章里曾写过:“当文化已经不是一个民族的思想和灵魂,而成为了政治斗争和阶级搏杀的工具时,文人手中的狼毫才成了血淋淋的屠刀和能致人于死命的尖刺。”
文学是思想的结晶,任何卓有才华的作家的生花妙笔,只有附丽在思想的土地上耕耘,才能生产出养育人类的精神食粮。没有自己独立思想的作家,即使是著作等身,或许能获取天文数字的版税,能使自己现实生活过得很滋润,但这些著作即便不是垃圾,也全部是废纸,与己有利,于人无益。
我期待着有一天,我们中华大地上,真正地迎来百花齐放的春天。也许我的生命在哪个春天的来临之前就完结了,但是我对文学的不结情缘是不会因为肉体的消亡就终结了的。因为我的灵魂不会死去,融入了我灵魂的不结情缘也永远不会死的……
近百年来,华语文学为什么鲜见有震撼力的文学作品,就是我们的民族生病了,需要救赎了,如此我曾萌生了一个要去“打劫生辰纲”的奇葩想法,幻想自己能发一笔横财后去创立一个奖项。这个奖项就叫“华语文学救赎奖”。奖金额要略高于中国大陆的那个“茅盾文学奖”。这曾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个夙愿,至于此生能不能完成这个夙愿,这就要看我的造化了。也许能,也许我死了也未能如遂心愿。倘是那样的话,我至死都不会闭眼啊!
其实在我的心目中,对于获得什么文学奖,根本就毫无意趣,我执著地认为这种光环其实都是过眼浮云,根本就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获奖与否,根本就不能体现出真正的艺术价值。即便就是被世界各国文坛都倍加推崇的“诺贝尔文学奖”,不也就是几个昏聩的瑞典老头率性所为而玩的纸牌游戏么?这个大奖,除了真金白银钱是真多真丰厚之外,真有独一无二的权威么?世界上的一流作家,有多少是诺奖遗珠?又有多少二流甚至三流的作家,也幸运地拿了奖,这难道还用我一一例举吗?
在这篇议论公元二十世纪汉语文坛样貌的文章里,我钦佩马建先生直面人生的勇气,我当然也该指名道姓地给诸多大作家们画画脸谱的。况且对主流文化的叛逆和“狂悖”,则本来就是我的德行!借此就算是出一口积郁在胸不吐不快的怨气吧!
首当其冲,我要评价的就是自称是500年间白话文第一人的台湾著名作家毒舌李敖,李敖以精通西毒欧阳锋“蛤蟆功”出名。李敖自我吹嘘他施展“蛤蟆功”,骂惨了大“独裁者”蒋中正;但在中华民族更大更残暴的“独裁者”“毛腊肉”面前,李敖却低眉顺眼似乎就是一个甘受凌辱和蹂躏的“小媳妇”儿,从来对中共的威权统治,不置一词。我是真不知道,这500年间白话文第一人的李毒舌,脊梁骨是不是已经弯了?还有享誉“台湾第一才女”之称的琼瑶女士,据说琼瑶女士一生出版了百余部长篇小说,但我同样不愿意探讨,假如琼瑶女士后来的丈夫不是出版家平鑫涛,还会不会有出版人甘做琼瑶女士的拥趸。
评价完台湾文化圈,再来回看大陆,茅盾和巴金当然算是有大成就的作家,但论及文人的风骨,他们比较沈从文先生,差得就太远了,他们霸占中国大陆汉语文坛数十年,尸位素餐就不必说了,但“贪图富贵生媚骨”就令人所不齿了。还有在大陆汉语文坛。流行的相互“捧臭脚,抬轿子”的糜烂之风,也“奇臭不可闻也”。靠裙带关系上位也令人不屑一顾。王安忆因为是诗书传家。理所当然是集大成者,或恐还能说服人;但贾浅浅就因为有个当作协副主席的老爸。她的“屎尿诗”也就成了诗品中的“珍馐”了,这难道不是咄咄怪事吗?
当然在我心目中,20世纪的汉语文坛,绝不是一无是处。我心目中当然也有心仪的作家。诸如金庸,虽然有人谴责他似乎忘了家仇国恨,但我对其文学造诣,确实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还有王朔这个痞子作家,尽管很多读者都认为他的语言很粗俗,但我依然爱不释手。即便就是曾被曹长青先生谴责为“假货”的青年作家韩寒,我就凭借他这句话:“什么圈到头来只能是花圈;什么坛到头来都是祭坛。”也认定了韩寒不是石头,而是金子!他就是我中华民族不可多得的青年才俊!
这篇文章啰哩啰嗦地已经超过万字了吧?就此打住吧!最后用我老家中国东北地区流行的小曲,结束这篇或恐会流传后世的文章吧!
“提起了庄老三啊!在铁板上种大烟,殚精竭虑七十年,生个赔钱的女婵娟……”
庄晓斌
2025年7月18日于法国兰斯
(文章仅代表作者 的观点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