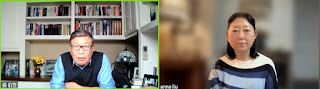锡安教会与中国家庭教会的见证
—— 张伯笠牧师专访金明日牧师妻子刘安娜师母
时间:2025 年 10 月 14 日
记录整理:对华援助协会
锡安教会 2017 年由金明日牧师在北京创立,2018 年 9 月 9 日被取缔。疫情后,教会全面崛起,在四十个城市建立100家教会。 2025年10月9日开始,三天内,22 位牧者及服侍成员被带走。 2025 年 10 月 14 日,采访视频 美国张伯笠牧师对金明日牧师的妻子刘安娜师母进行了访谈:
壹、风暴前的预感
张伯笠牧师:这次事件发生之前,金明日牧师是否有预感?
刘安娜师母:是的,有两个征兆。
第一,半年前金牧师给我看过一份文件,是东北某县级市一家公司发出的通知,内容明确提到金明日是谁,做过什么事,并警告职工不得与他接触,有种“定罪式”的语气,让我们警觉起来。
第二,金牧师从 2018 年就被边控,为期五年。原本 2024 年 4 月应该结束,结果 4 月 24 日他前往越南边境时再次被告知延期,这也让他意识到局势不妙。
贰、教会的起伏与转型
张:你们分隔两地都七年了。他过去是拿十年签证。你们如何保持联系,是透过网络吗?
刘:中国屏蔽了WhatSapp Singnal这类通讯软件,我们有自己开发的 APP 。我们曾用过四五种平台,但几乎都被关停了。
张:锡安教会什么时候被全面封禁?
刘:2018 年 9 月 9 日,之后锡安教会无法再租借聚会场所,正式进入流动聚会时期。我们变成“行走的敬拜者”,会事先录制敬拜内容、大家在公园戴耳机绕行,参与四十分钟的行走礼拜,之后大家一起喝茶、感恩分享,一段时间仍然坚持着。
张:这种型态真是另类的坚持。后来是否尝试使用 Zoom?
刘:有的,特别是疫情期间,我们建立了技术团队,推动网络聚会,也进行周一联祷会。这个过程对信徒的连结非常重要。
叁、从北京出发的宣教旅程
张:后来他去了北海,是主动离开北京的吗?
刘:是的。 2019 年后北京环境恶化,反正他孤家寡人了,去哪都自由,无牵挂了。他便开始主动拓展,2022 年夏天定居广西北海。在此之前,他也曾前往广州、深圳、珠海建立小组与教会,灵活、机动,找到驻堂牧者进行区域化牧养。珠江三角洲,分一个片,有牧灵的牧师。王林牧师则去了上海。
肆、与金牧师的相识与信仰之路
张:您和金牧师是怎么认识的?
刘:我们高中时在黑龙江认识,他是借读生,我是学生会文艺委员,他是主席,从那时就有交情。我们都是第一代基督徒,1989年六四事件后信主。
张:那时你们对信仰的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刘:对我们来说,那个年代的成长背景就是——我们热爱党,也热爱国家。即使在 1989 年「六四」发生时,我们的诉求并不是推翻共产党,而是希望国家能够反腐,变得更好。我们没有任何宗教背景,是在红旗下长大的第一代青年。
后来来到北大,一切开始改变。 1986 年的学潮对我们这一代学生影响很大。原本接受的教育几乎都是灌输式的,但进入北大后,我们开始学会独立思考,开始思索:中国要往哪里走?怎样的制度才是最适合中国的?这个寻找的过程非常痛苦。
我和金牧师是朝鲜族,当年我们虽不是学运中最积极的份子,但也有着相似的渴望和梦想。六四事件对我们两人都是极大的冲击。我读心理学,但那段经历成了我心里的一个创伤,导致我长期逃避与六四相关的内容。那次梦想的破灭,超出了我们所能理解的范围,留下了难以承受的现实。但我们知道——我们还得活下去。
有一位姐妹,那时特别关心金牧师。她是我们少数民族中的一员,也是朝鲜族。那时在北京,朝鲜族很少。有一次我搭公交车,突然听到有人讲朝鲜语,激动到坐过了站。那位姐妹曾邀请他吃饭,在六四期间为他的安危不断祷告。后来她因胃癌去世,但在病痛中始终纪念并为他祈祷。她的信仰和爱深深触动了我们。
就是在她的葬礼上,他第一次遇见了耶稣。之后,我们开始走进教会。金牧师比我早一步回到北京,也是在那时,他告诉我:他信耶稣了,而且特别渴望成为一位牧师。
当时我心里想:「这个人是不是脑子坏了?怎么突然变成这样?」我去教会是为了「把他救回来」,我试着找出信仰的漏洞以便把他抢回来。
伍、走上全职服事与三自的挣扎
张牧师:六四那代人,很多人患有不同程度的创伤综合症。我们这些曾经坐牢、妻离子散的代价更重一些。但这一代人多半会认真思考信仰的前路。我们那一片地区后来有很多人信主。
师母:在六四之前,去缸瓦市教会的人可能只有一两位,但慢慢地发展到五、六十人。其中绝大多数后来都成了牧师。像金天明、李圣风牧师,也都是从缸瓦市出来的。
张:那时候结婚了没有?
刘师母:还没有,信耶稣又不挣钱,怎么结婚?父母当然不同意。他为了现实考量,在外企工作了两年。当时中韩刚建交,懂汉语的工作机会也不少。我们是在 1992 年结婚的,一月结婚,五月他就去读神学了。
张牧师:那你当时有什么反应?
刘师母:我家属于朝鲜族家庭,气氛比较开放,我没受到什么资源剥夺。父亲思想也很开明,我也认为人生是自己的,要自己负责。他的选择我也不好干涉。我当时其实不认为「牧师」是个好职业,但我也说,如果你真有感动就去试试,如果不合适,早点回头也可以。
张牧师:当时你不知道当牧师还有坐牢的风险吧?
刘师母:完全不知道。结婚之后,才慢慢明白,原来作为牧师的妻子,是要承担许多代价的。尤其是「师母」这个身份,大家对师母有很多期待,但我对自己却没有那么高的认知,这之间其实有很大的张力。
张牧师:我家张师母也是,当初有人叫她师母,她都不知道那人在叫她。你们在加州工作吗?
刘师母:我们参加韩国教会,韩国教会的师母其实挺辛苦的。
张牧师:我认识金牧师,是他在富勒神学院(Fuller)读书时。有一次我们一起搭车,从南加州开到北加州参加婚礼。当时才知道他是北大毕业的,感觉一下子拉近了距离。
师母:我们这一代朝鲜族信主,大多都是六四之后。金牧师是在参加那位姊妹的丧礼时信主的。后来我们联系上缸瓦市堂,想走传道人的路,就需要去崇文门受培训。不过“三自”系统对他一直存疑——神学院里没有他这种学历的,一个北大地球物理系毕业的,还接受过外国宣教士装备的,他们会怀疑你到底有什么「居心」来参与三自。
但金牧师始终相信:上帝呼召他在哪里,他就应该在哪里服事。神让他进入三自神学院,他就忠心地服事了十年。但这十年并不好过,常常被排挤、打压,真的一言难尽。 2002年,他实在撑不下去了,选择离开,算是一种缓和。
当时宗教局还派他去朝语堂,但那是个权力角力的地方,他很辛苦。他想多付出,但总有人在后头拉着,权力文化很重。
张牧师:是啊,他不太了解中国教会的内部生态,很难融入。他那种背景的人,他们特别警惕。
陆、美国装备与归国宣教
刘师母:后来他决定出国,但三自当然不乐意。北大毕业后,他的档案无法由三自掌控,只能放到「国际人才交流中心」,三自也就无从干预了。护照由国际人才办理的,签证更不在三自手上,于是他在 3 月出国,5 月拿到签证,那段时间他靠打两份工生活。
张牧师:他在美国有参与华人教会的服事吗?
刘师母:我们那时候主要参加洛杉矶的韩国教会。他是朝鲜族牧师,虽然中文讲得很好,但更习惯用韩文服事。我们一边在教会、一边在机构工作。他后来完成了教牧博士学位。
张:毕业后,回北京参与了城市家庭教会,教会起初的情况如何?
刘:金牧师回国,他不想参加三自,他是被三自按立的牧师,他知道不参与三自,有代价,参与三自也要付代价。不参加的代价他愿意承受。
张:成立时有无注册?
刘牧师:政府要求注册是个幌子,守望去注册没有成功。没有成功是因为没有“合法”的传道人,他们说:金牧师你去试试。其实不是你有这个身份,就能注册,它没有让你成功。家庭教会不注册,不在三自之下。
2007 年开始,许多神迹奇事发生。我不喜欢做师母,我希望他做神学院的老师。但有信徒找到我们说,我们开始祷告吧,于是我们从三月开始为这事祷告,五月聚会逐渐形成。早期以朝鲜族为主,后来扩展到汉语堂,是双语聚会。
柒、从城市教会到网络聚会
张:你们属于“城市家庭教会”的代表,是否政府早有关注?
刘:政府对网络和线下的结合非常警惕。新的网络管理条例,我们意识到打压即将升级。
张:秋雨、守望、金灯台教会都曾被打压,为什么秋雨的王牧师当年被判,金牧师没有被判?这波似乎是全面清理。
刘:锡安其实从 2018 年就开始被针对。他不那么公开抗争,金牧师一直以温和、愿意沟通的姿态面对政府,但结果一样。
捌、突如其来的抓捕
张:他是怎么被抓的?警察当着你妈妈的面把他带走。
刘:当时吃完饭,十多人闯入,手机、电脑全被带走,书房和整个家都被查封。我的母亲已近80 岁,受了很大惊吓。女婿这么善良,没有跟人红过脸,不说人坏话,就是传福音。我说,金牧师自己有预期,你若病倒了,我们更惦记,为了我们也要保重自己。金牧师现被指“涉嫌非法利用网络信息”,被羁押在北海第二看守所。
张:孩子知道了吗?
刘:知道。我们的女儿 Grace 目前在美国参议院工作。来自 AP、BBC、德国报刊等国际媒体都有关注,国务卿卢比奥也在呼吁中国政府释放他。
玖、面对逼迫的见证
张:你心理学背景是否帮助你面对这些?
刘:我努力在内心接受事实,然后思考如何以合乎信仰的方式回应。不是不愤怒,但要知道如何把这些转化为基督徒的见证。我们活着,是为了荣耀主。
拾、结语:与中国教会同站
张:我们知道你压力很大,还有要照顾老母亲。我们愿意与你同行。
刘: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在联祷会中彼此鼓励,看见神正在兴起一批成熟、坚韧的基督徒。这不是锡安一间教会的事,而是中国教会整体的属灵复兴与争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