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云 低音 2025-11-17 | 转自 新世纪
过去一个月,“稀土”成为了拉扯许久的中美贸易战中的热门关键词。中国商务部在10月6日突然连续发布6项公告,宣布升级稀土出口管制。按照公告内容,只要产品含有、集成或者混有价值比例0.1%以上来自中国的稀土,境外组织或个人均需要向中国商务部申请获得审批文件——按此说法,这些产品包括特斯拉的电动车、苹果的手机和英伟达的芯片。
美国总统特朗普立刻宣布对中国产品加征额外100%关税,并推进了澳大利亚、日本、巴基斯坦等国的矿产协议或稀土开发计划。10月30日,特朗普与习近平在韩国APEC峰会上会面。中国在此次谈判后宣布暂停执行10月颁布的稀土出口管制措施。
在今天这个时代,稀土已经变得不可或缺。它们既能在工业生产中作为催化剂使用,也在电动汽车、电子、光伏、风力发电等众多新兴产业中被广泛使用。中国之所以能够在贸易战中打出这张“稀土牌”,也是因为中国已然在全球稀土行业取得了垄断性的地位。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矿产品概要2025》报告数据,目前全球稀土储量超过9000万吨,其中中国就拥有4400万吨储量,占比接近一半。具体到实际的生产量,2023、2024这两年,全球分别生产了37.6万吨与39万吨稀土,其中分别有25.5万吨与27万吨来自中国,占比分别达到68%和69%。《纽约时报》更是报道称,欧盟约98%的关键稀土进口来自中国,美国则有80%的相关稀土从中国进口。
事实上,中国也不是第一次利用在稀土行业的垄断地位对外施压。早在2010年,中日双方在钓鱼岛附近发生撞船事故后,中国就通过海关部门禁止了稀土产品出口至日本。2019年的中美贸易战期间,中国官方也多次威胁要断供稀土作为反制,譬如发改委官员就曾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如果有谁想利用我们出口稀土所制造的产品,反用于遏制打压中国的发展,那么我想赣南原中央苏区人民、中国人民,都会不高兴的。”当时,习近平刚刚视察了位于赣南的稀土企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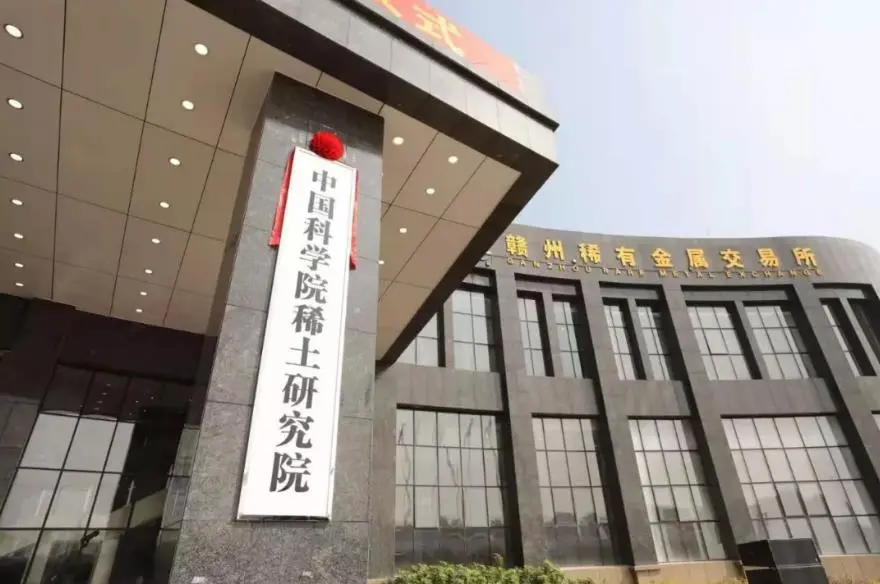
图:位于赣州的中国科学院稀土研究院。来源:中国科学院网站
稀土全称“稀土元素”,是17种金属化学元素的合称。但稀土在地壳中的含量本身并不低,譬如含量最高的铈,在地壳中的元素丰度排名为第25位,占地壳的66ppm。接近于铜的68ppm,甚至是铅的5倍。
困扰稀土开发的原因主要在于两点,一是稀土元素的化学特点导致它们往往难以富集为单一矿体,无法像铁矿、铜矿等可以直接开采;二是稀土元素们由于化学性质接近,通常会在矿床中共生,难以分离、提取。
中国的稀土产业从70年代开始发展,为什么能够上演“逆袭”?
在一些官方媒体的叙事里,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被称为“中国稀土之父”的徐光宪。徐光宪在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化学部院士,他提出和研发的稀土“串级萃取技术”,让中国的稀土分离技术在全球范围取得了领先。《科学时报》2008年的一篇报道称,在徐光宪带来的技术突破帮助下,“中国终于实现了由稀土资源大国向稀土生产大国、稀土出口大国的转变”,“上世纪90年代初,由于我国单一高纯稀土大量出口,使国际单一稀土价格大幅下降,原来曾经长期垄断稀土国际市场的一些国外稀土生产厂商不得不减产、转产甚至停产。”
除此之外,还有宽松的环保监管环境和低廉的电力、人工成本。
稀土产业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想要实现分离矿物中共生的各种稀土元素,往往需要大量硫酸铵、氯化铵等化学物质进行反应,导致包括氟化氢、硫酸、二氧化硫和氨等污染物的大量排放——曾是全球最大稀土矿场的美国加州芒廷帕斯矿,就曾因为污染问题引发大量抗议而关停。
原本垄断全球稀土产业的欧美国家,在政府与民间的双重挤压之下,稀土企业承担着巨大的舆论压力与居高不下的各种成本。而在另一边,刚刚重新回到全球市场的中国,却在环保几乎毫无监管、人力成本极低的背景下,实现了关键的技术突破,中国制造、价廉物美的稀土,顺理成章地占领了几乎整个市场。

图:美国加州芒廷帕斯矿。来源:Wikipedia
那么代价是什么呢?
早在2006年,《扬子晚报》就发过一篇名为《包钢尾矿坝污染调查 放射性毒水向黄河渗透》的报道。文章提到,在内蒙古包头市有一座世界上最大的“稀土湖”——也就是尾矿坝,包钢从白云鄂博采到的稀土矿,会在包头的选矿厂中研磨,最后分离出10%稀土,其余矿浆则全部会被送到尾矿坝,其中包括含有大量放射性金属钍的稀土。
报道还引述当地医生指出,尾矿坝周边的一个村子,骨质疏松、半身不遂的患者正不断增加。从1993年至2005年底就有66人死于癌症;2006年以来,全村14名死亡村民中,有11人死于癌症。
这篇报道发出的前一年,中国科学院院刊也曾刊登一篇名为《关于保护白云鄂博矿钍和稀土资源 避免黄河和包头受放射性污染的紧急呼吁》的文章,提到“包钢三废排放含有放射性钍的废气、尾矿飞尘、废水和废渣,不但严重污染包头地区,而且是黄河的主要污染源之一……钍的回收、尾矿坝的保护和三废治理不可再延缓”。
《南德意志报》记者今年前往上文提及的“尾矿坝”调查发现,这片“稀土湖”的面积已达12平方公里——接近两个杭州西湖的大小,且距离黄河不到10公里。每年预计会有600至800万吨含有重金属、酸液和放射性物质的泥浆被送进这片“稀土湖”。
但无论是官方报道还是社交媒体,关于尾矿坝污染来源的白云鄂博矿区,最多人提到的词是“世界稀土之都”、“全球最大的稀土矿床”、“沉睡了亿万年的神山”。
而中国南方最大的稀土产区江西赣州,更是经历过一场疯狂的“搬山运动”。由于当地的稀土矿床大多露天,易于开采,当地政府与投机者不断涌入,起初采用的“池浸法”工艺,需要先砍树后锄草,然后剥离表层土壤,大量稀土矿就这样被开采、废弃,山体植被则遭受难以修复的破坏。在最巅峰的时期,赣州拥有超过1000个大小不一的稀土矿采矿点。
2012年,《经济参考报》的一篇报道引述时任工信部副部长苏波的发言提到,当时采用的“原地浸矿法”,1吨氧化物的开采需要注入7、8吨的硫酸氨,“这些有毒的溶液长期残留地下,一旦污染地下水资源后果不堪设想”。苏波还提到,初步测算,仅赣州一地因为稀土开采造成的环境污染,矿山环境恢复性治理费用就高达380亿元。
事实上,影响可能已经出现。2023年,赣南医学院的几名作者发表了一篇名为《江西某废弃稀土矿周边土壤重金属污染及居民慢性病患病情况》的论文,提到“根据水土流向,从上游矿区到下游矿区周边农田,各种金属含量(尤其是铅)均呈现一定累积上升趋势”、“相较非矿区周边农田,矿区周边农田土壤中各种金属含量相对较高”。
BBC也在今年的实地采访中,引述《稀土前沿》的作者克林格教授的说法称,在2010年前的数十年间,稀土矿区附近的村民被诊断出骨骼与关节畸形,原因是水中氟化物含量过高,还有一些是急性砷中毒的案例。
因为稀土,广西玉龙还曾发生过一场抗议。2018年,广西玉龙村民因为认为新开的稀土矿项目接近水源,且环评可能涉嫌造假,展开了一场持续的抗议,结果是抗议还在持续,工地已经挖出了十几个大坑。一次与警方发生的冲突中,16名村民被带走,这场抗议也没有再引起更多波澜。

图:稀土之都内蒙古包头。来源:Guardian
科技产业的发展和地缘政治的紧张,让稀土的重要性大增,一场新的“合谋”也在出现。
全球化时代的“合谋”,是在持续超过二十年的产业转移浪潮下,中国赢得了稀土产业的绝对垄断,全球的汽车、互联网乃至今天的人工智能巨头们,则得到了中国的廉价稀土供应。只是它们未曾预想的,是全球化时代造成的垄断地位,恰好在这个去全球化时代成了中国的砝码。
这场新的“合谋”,却将更多国家卷入了一场划分地盘式的战争中。从巴基斯坦、日本、澳大利亚乃至乌克兰,稀土往往会成为特朗普谈判桌上的筹码,换取的可能是现金、关税或者军事援助。而对于中国来说,在稀土已经上升到国家安全的层面之后,继续维持在全球稀土产业的垄断成为必选项。于是,中国央企在老挝投资2100万美元控股了一家稀土矿场——去年2月,该矿场发生的化学物质泄漏事故,污染了当地的河流并导致数人患病,引发了当地村民的激烈抗议。
各国政府和资本都在积极加入稀土经济。在一篇分析非洲稀土产业潜力的文章中,作者预测,“到2029年…非洲生产的稀土将会满足世界10%的需求。”文章还提到,科技富豪杰夫・贝索斯和比尔・盖茨都已投资了在非洲开采稀土的公司。但文章没有提到稀土开采带来的污染。
2019年,耶鲁大学环境学院的网络杂志E360发表了关于中国稀土开采污染的文章,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接受采访时表达了担忧,世界其他地区可能会重走中国的老路,以环境污染为代价,换取稀土开采,“听说在非洲和其他地方可能开始有类似的开采,所以我们不能再犯一样的错误。”
他的担忧在一些地区已经变成现实。今年9月,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发布一份调查报告,称稀土开采正在破坏湄公河流域环境。上游缅甸境内的开采活动产生的有毒废物污染了河流,并流入泰国。当地居民赖以生存的渔业遭到破坏,农作物无法进入市场售卖。更有民众担心,当地唯一水源遭到污染后,他们在明年旱季的饮水将无法得到保障。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