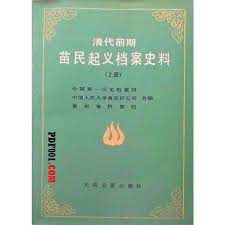来源:作者田老师
生苗族群的存在条件,一是广阔的无主土地,二是不相统属的议榔。湘西生苗在腊尔山区,其地朝廷不愿管理,筑墙以隔,生苗也认为该地属无主土地。但自从“开辟苗疆”以后到乾隆六十年共九十年间,生苗区的土地私有化过程已经完成并不可逆转,生苗生存的经济基础不复存在,与之相对应的议榔制度及相关榔款也必将土崩瓦解。本篇读书笔记将谈一谈湘西生苗的议榔制度瓦解的过程。
该文的资料来源于《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贵州省档案合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以下简称《档案》。
- 议榔的局限性
“议榔”是苗语,意译为盟誓会议。指不同宗支的村寨集合而成的地缘性公社,即相邻的村寨之间形成的社会自治机构。
生苗期间,一般是单姓寨,寨内人为同一宗支。后来,因姻亲关系,出现了复姓寨。再后来,因汉民的进入,又有了民族杂居的寨。但议榔组织的形式未变。
议榔在湘西多称“合教”。其组织大小不一,有几寨,几十寨构成不等。其成员,必须服从榔款,即公约。不同意榔款的,可搬家至他处。议榔成员绝对不能违背榔款,若违背必受警告、教育、处罚酒、罚肉、直至处死。
议榔、榔款,属于习惯法的范畴。其产生、执行、监督、处罚都有固定的仪式。
湘西生苗区有数千苗寨,却没有统一的政治组织和行政机构。整个生苗区的社会管理都是通过无数独立的议榔组织完成。
每一个议榔组织内部成员,一般都能自觉遵守榔款。所以,在生苗区,每一个苗寨的内部管理是有序的。比如:保护公共水源、禁盗抢等社会治安、村民互助、打冤家等等。但是,对议榔组织外的成员,榔款是没有约束力的。遇议榔组织外的盗抢行为,只能通过协商处理,协商不成,便“打冤家”,即两个寨或两个议榔组织之间的械斗不可避免。议榔组织内部成员在议榔组织以外的行为,比如在外盗抢,榔款则是不禁止的。所以,生苗区的各个议榔组织之间的纷争,是绝对禁止不了的。这便是生苗区的社会管理制度无统属的后果。
当代的研究表明,人类的道德规范、法律规范,大部分形成于私有制确立之后。人类的普世价值观,无争议的部分是对人的自由、生命、私有财产的保护。而生苗存在的时期,应是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军事化时代。生苗所能理解的私有财产,无非是工具、食物、住房等动产,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资源,一是宗支,二是议榔。最大宗的生产资料——土地没有私有化,因此根本形成不了完整的私有财产观念,更不能形成合理的财产保护制度。这种原始、野蛮的习惯法,在土地私有化已经形成的乾嘉年间,必将与当时的主流文明发生剧烈的冲突。
- 乾嘉苗变榔款的形成。
有研究者认为:乾嘉苗变前,苗酋们进行了八年的议榔才形成此共识。八年,即时从乾隆五十二年勾补寨石满宜事件开始,至乾隆六十年。但《档案》显示的时间,是乾隆五十九年底至乾隆六十年正月。
乾隆五十九年十月,腊尔山各地有苗人“发癫”,传言“苗家要做官”、“要杀客家,夺回田地”、“苗家里要出苗王”等等。
参加合款的主要苗酋即榔头:黄瓜寨的石三保,大寨营的石柳邓,鸭堡寨的吴陇登,苏麻河的吴天半,平陇的吴八月父子。先后参与合款的苗酋近百人。
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榔头们在鸭堡寨土地庙歃血结盟。
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榔头们正在乾州强虎哨山三王庙内歃血结盟。
乾隆六十年正月初四,榔头们在黄瓜寨正式合款,由吴八月书写传贴,确定二月初六(苗年正月初一)起事。石三保自称第一代苗王——吴王。
合款的主要内容:乾隆六十年二月初六,各自在自己的范围内,杀汉百户,烧汉人房屋,抢汉人钱米财物。
会议没有形成统一指挥的机构,没有确认最高统帅。而是沿用苗族古老的习惯,各寨苗酋带领各自苗众就地起事。石三保自称苗王,也只是象征性的,除了黄瓜寨附近的苗众可供其指挥以外,其他苗地的苗人,他也指挥不了。“各路苗子有各路的头人,各寨的苗子又有各寨的头人,也不是小的一个人叫得动的”(石三保供词)从“开辟苗疆”到乾嘉苗变已九十年,苗区内的苗寨“小而散”的状况也有了根本性的改观。由于水田的开垦和交易的频繁,逐步形成了很多的百户以上的大寨,于是也给议榔组织形式带来很大的变化:以大寨为中心,与周边小寨形成固定的议榔组织。当时叫做“小寨并大寨”。
违反榔款的后果:
“如有不从的,就先烧他的寨子”(吴天半供词)
“……吴陇登不允,石柳邓们就要烧抢,他儿子吴老管、吴老黄即吴老五、吴老铁应允,就吃了血酒”(杨国安供词)
“(从石柳邓、石三保)叫我们做他的人马,我们不肯从他,就要烧杀我们,我们害怕,就依从了……”(陇九生供词)
“石柳邓查的很紧,声言凡有苗子如有出来投降的,他就先烧他的寨子,杀他的家口”(张士发供词)
“……不从石柳邓的,便被抢杀,人人畏惧”(田庆禄供词)
“我们甑子寨本来离黄瓜寨只有十多里,若不肯帮他(石三保——引者注),他就先要把我们杀害,所以不敢不依他”(陇老章供词)
从“开辟苗疆”到乾嘉苗变九十年间,苗人中形成了一小部分的“富苗”、“强苗”。起事首倡之人便是“强苗”、“富民”。这些“强苗”、“富苗”控制了大苗寨,大苗寨又控制了小苗寨。这样,整个苗区“起事”的合款就形成了。
与“开辟苗疆”前的议榔组织制度不同的是,以前不同意榔款的可以退出,(这也是生苗区分寨的原因之一)而现在,不同意榔款的无处可以安生。无主土地已经消失。生苗因被汉人歧视,不愿意去汉人区生活。小寨只得无条件服从大寨的款约。因此,乾嘉起事的合款,是“强苗”、“富苗”的裹胁所致。但是,这绝对符合苗族古老的习惯法。既盟约发誓,喝了血酒,就只能照款约行事,绝不反悔。
- 降苗的过程
乾隆六十年正月十五,因石柳邓被人告密,大寨营被清兵镇压,起事提前至正月十八。
云贵总督康福安于乾隆六十年二月十四日率清军主力抵达铜仁,二月二十日解围正大营,闰二月上旬解围嗅脑,闰二月十四日解围松桃。四川总督和琳率兵赶到秀山后,与康福安合兵,于闰二月二十八日攻占了大寨营。“三月,贵州苗略定”。
清兵攻解嗅脑后,“即有苗头贯百户率领陇保二、陇老金、陇仁贵等来营迎接(叩头),据称实系良苗,并称伊等附近一带,苗民均未从贼,前因大路阻塞,不敢前来。今见大兵痛剿,城解路通,俱欲请旗效顺”,“次日果同虾公坳等十寨头人陇老衰等,各率所管苗户,来臣营盘,哀号乞命”。
清兵攻解松桃后,“复有上下长坪等二十一寨百户、头人吴胜文等,来营恳请赏旗”。
乾隆六十年闰二月十九日,“麦地汛各寨苗民又叩头乞命,并请修整桥梁道路……铜仁、正大之间,有虾公溪苗百户陇老蟒、带领喇叭洞等四处百户头人来营:具呈投叩”。
以上,“投诚乞命已有六十五寨,户口二千一百八十余家”。
乾隆六十年闰二月二十五日,“连前次归降之六十五寨,已有二、三百寨,合计人口约三万有余”。
随着清军在松桃的军事目的依次实现,周边苗民便依次投降。清军主力入松桃一个半月后,即乾隆六十年三月,松桃境内基本平静。
松桃苗民没有不战而降的,也没有临阵投降的。都是因战败而不能逆转的情况下投降。起事初期,石三保派了大量的湘西苗民由石柳邓指挥在松桃打仗。最初投降的陇保二,被清廷赏了六品顶戴。“讵陇保二因住寨孤悬山顶,回寨后被石三保等知觉,率领逆苗,将该寨围烧殆尽,陇保二被杀身死”。终因清军过于强大,湘西苗民退回湖南,大量松桃苗民投降。
松桃苗情稍安后,乾隆六十年三月清军主力开始进入湘西,三月十五日攻解永绥。但在清军主力尚未进入湘西的乾隆六十年闰二月十三日,乾州轨者寨百户石上进、赛阳寨耆保杨鼎元派人到辰州府递送投诚禀帖。二月十七,石上进、杨鼎元经传唤面呈降意,并献出愿降四十二寨清单。三月初十,石上进、杨鼎元等十二名头人,来到辰郡,称:“小的们到了赛阳寨,将各寨传齐,并有闻风而至茶叶坪等十四寨,情愿相率投诚,公同与差去外委滕茂才等吃了血酒,散给良苗旗号。还在商量启程间,被逆苗捉获民人张廷禄问出各寨投诚情由,聚集多人,攻打了石上进所居轨者寨。小的们力量不能抵拒,被其焚烧,率领子侄并保护外委滕茂才、差役罗忠,田良连夜逃出,其他各寨均在竭力堵守,以待大兵”。
据《乾州厅治》(清•同治)载“轨者山,城西三十五里……下有苗寨名鬼寨。轨鬼音近,苗俗畏鬼,改名矮寨”。赛阳,即寨阳。据《苗防备览》载:“上下寨阳,城西北二十五里,熟苗”。
轨者寨被烧,是对降苗石上进的惩罚,是执行榔款。而赛阳是熟苗,没参加议榔,不是榔款的执行对象。
乾隆六十年四月中旬,黄瓜寨被清军攻陷,失去寨子的石三保,成了光杆司令,隐藏于半冲、龙牙。没有人出面对降苗实施惩罚。
乾隆六十年六月:“……旦营等十五寨,……板梨坪等十三寨……新寨等十二寨……石大贵等六十八寨……通计前后已降苗寨一百五十处”。
以上地乾州西北境与永顺(现古丈)、保靖境等交界处。多在边墙之外,多为熟苗。
黄瓜寨被清兵攻陷后,腊尔山台地开始出现降苗。当清兵驻扎乌巢河时,有“百户等递禀,情愿乞降”,而清军以“务将首恶擒缚前来,方准赦其前罪”。于是,暗地投降帮清军报信的日益增多,使抵抗清兵的苗人不断遭到重大挫伤。
乾隆六十年六月,永绥隆团(今龙潭)窝坨寨石老观带领苗人抵抗,清兵“令降苗石文茂、杨光祖设法擒献,抚以恩信,该降苗等竟将该犯乘间缚送,并将屡降复叛之小排吾头人麻章保—并拿解前来……隆团一带逆苗亦渐形敛迹”。
乾隆六十年六月十二日,“前派密访首逆踪迹之降苗百户吴清德等,查得吴天半现在板凳寨附近……兹既得有踪迹,立刻带兵前进”,十三日,吴天半遭重创,死里逃生。同日,在捍子坳,两三千苗人“到被焚烧降苗寨落,遭清兵夹攻”。“各官兵无不奋勇争先,附近降苗亦俱痛恨贼苗,实力随同剿杀”。“ 贼匪不敢抵御,旋即溃败”。
六月十七日,“适据降苗百户报称,访得吴天半前被官兵剿攻,痛恨降苗报信,现由雷公滩纠众前来,愤欲报仇筹情”,清兵立即安排“兵丁及出力降苗设伏”。十八日,吴天半率领五、六千人果中伏击,战至二十一日,退至雷公滩山坡,沿途拼命抵抗的万余苗众,终被三路官兵冲作数截,由东山梁一路逃散。
“其夯柳苗人因见官兵势大,俱抛掷器械,齐声呐喊,情愿投降。该道等不准所请,仍督率备兵齐力追击。贼众纷纷逃窜”,为此,清廷专有谕批“遇有此等剿败贼匪临阵乞降者,俱照常明所办,毋得率行允准,以防反侧”。同年八月初九,《渝福康安等苗众乞降自应允准》“附近苗匪多有长跪山巅乞降,并有情愿跟随打仗、守卡修路,以图赎罪者,此最好之机。福康安等暂准降顺,以分贼势,正宜如此为理”。
乾隆六十年八月二十七日:“两三日间,统查投降苗寨大小共七十多处……均系著名紧要寨落”。
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九:“新降二百二十七寨”。
“凡是预先投降者,福中堂和大人准他降顺,如系,临阵投降者,福中堂和大人因他们系打败仗,其心不恻,概不受降,仍旧剿杀”。
乾隆六十年九月二十日,“探访得首逆吴天半从鸭堡寨来至高多寨”,清兵“四面严密攻围”。吴天半见状,“带同伙苗二名,直指军前,自行投首”。
乾隆六十年九月二十八日,清兵攻克龙角峒,自辰至酉,“旋见无数贼苗,长跪石城内高皋处所,“成称情愿投降,恳求饶命。其中老幼男女,俱俯伏叩头,痛苦呼号”。“臣等不准投降,仍严督各兵悉力攻击”。“其附近未经剿之十五寨落,俱即相率相投”。清廷称“不准苗众投降甚为得当”。
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初二,吴八月在廊家寨被吴陇登诱捕。
“吴陇登自吴天半被擒之后,曾密求降苗代为乞命”,“督兵擒捕吴八月之时,吴陇登亦曾密令廊家寨降苗陇老又等极力擒拿”,“再,查吴陇登-犯前于办理石满宜一案曾经出力,此次自臣等克黄瓜寨以后,该犯即有意出投,唯节次据称,恐一经投顺则各路逆苗必将伊寨落焚烧,争先仇杀。总俟大兵到日,再行立功自赎。”十一月十二日,吴八月之子吴廷义,率众苗乘间占据鸭堡寨,而且纵烧鸭堡一带寨落。撤回时,将坪朗、寨阳二寨降苗数十户全行烧毁(因降苗杨鼎元、杨正黄、侯忠词、杨老五等在相近寨阳地方,将石老四诱拿押送来辰)
清兵进攻地良坡一带,十二月初七鬼樊溪一带苗寨投降。十二月十一日:“据斗恩寨降苗陇老五等报,平陇各寨逆苗,定于十三日早晨齐集普定寨地方,有四、五千人,在彼立旗祭神……官兵冒雪骤至……毙贼极多,并生擒四十余名”。
清兵连克擒头坡、吉吉寨后,嘉庆元年正月,大陇洞、敢子坪、沙洛坪、斗角、岩尾坡、九十九洞投降,不下一千余户。
嘉庆元年四月初十,“吴陇登到营而降。后带领降苗三百余人,赶赴前敌随同打仗,极为出力”。
五月十二日,石三保在保靖哄哄寨被土蛮降苗计擒。
六月十七日,清兵收复乾州。
七月,“凡有降顺各苗,统计黔楚两省不下二十余万”。
七月十六日,清兵欲攻三岔坪,百户吴麻五等带领各寨头人投降。清兵答复:“如能前驱杀敌,方准立功自赎”。十八日,令百户带领降苗在前进发。平陇苗人得知三岔坪苗叛,欲烧三岔坪寨。两寨苗众厮杀。清兵四面围拢,枪炮并发,坪陇苗人四散奔逃,死伤惨重。
八月初九,清兵冲占强虎哨。“当有劳神寨、地村苗目吴老岩、吴老季至营乞命”。
八月十六日,石柳登手下大首领石代葛在率众袭击清军后路时,被降苗在永绥老旺寨抓获并押到大营。
十月十七日,清军攻陷坪陇。
至嘉庆二年三月,清军主力移至湖北。乾嘉苗变落幕。
四、议榔的嬗变
据苗族古老歌记载,议榔产生于苗族迁涉过程中。因苗族社会没有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苗族逃避抵制汉人的文化和统治,所以,苗族社会长期处于“有族属、无君长,有贫富、无贵贱”的“不相统属”的状态(魏源《圣武记》)。其社会各种组织均浓烈地延传着原始民主平等制的遗风。议榔,便是典型代表。
议榔的主要形式都是通过会议制定规约形成习惯法,其形成的榔款即公约,对内部职能主要是执行款规来体现的。因此,议榔制度是苗人处理其内部事务的公约组织。根据原始平等的理念,如不同意公约的,可另聚寨而居,一旦通过,死不反悔,并歃血盟誓。湘西生苗在腊尔山固定居住后,因与汉人隔绝,其议榔组织之间的矛盾,依靠议榔组织的力量平衡来解决,没有外部干涉的因素,议榔组织的重新组合是自发完成的。
乾嘉苗变“逐客民复故地”的榔款,是发生在“开辟苗疆”九十年之后,议榔存在的社会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土地私有化已经完成,游耕时代已经结束。抢夺命按大清律执行。汉人在腊尔山居民占百分之二十左右。主要居住在交通要道和水田众多的地方。腊尔山苗区土地被汉人侵占的情况是不均衡的。汉人民村和苗汉杂居的苗民及周边苗民迅速起事,但离汉人居住的民村较远的苗寨,就是“未剿未降”又“未变”的苗寨,在清兵进剿的情况下,是降还是不降?因此,“未降、未剿、未乱”的边远苗寨成了“降与不降”动摇人群。清军在强大的军事进剿的同时,广发文告,招降纳叛。苗兵首领也频频出人该动摇人群“邀人打仗”。吴天半、吴八月就是在“邀人打仗”途中被擒。
清廷认为:“由于被胁入伙者,均各情愿投降,求得生路。而自知罪不在赦者,逾图并力纠聚,抵死抗拒”。苗变之后,不战而降的是熟苗,因为熟苗区离政治经济中心近。而生苗区,因距清军主力远近和义苗主力远近啊剿动摇。“降”和“不降”,取决于生命安全的系数。如贵州苗,在松桃解危后,就是因为帮黔苗打仗的楚苗撤回湖南而选择投降,以避免无谓的牺牲。清军主力进入湖南后,采取“随剿随抚”的策略,所以,清军主力所到之处,尔后降苗遍地。清军与苗兵反复争斗之处,出现了“屡降复叛”的苗酋。
坚持抵抗的吴天半、吴八月们,面对公开的清兵和降苗,还要提防暗地投降的降苗,这样就造成了战略纵深极大的萎缩。生苗在明朝发明的游击战亦不能上演,被迫改变为阵地战,恰好扬敌之长显己之短。加上对降苗的报复,加速了民族撕裂,而且损失兵力惨重。与明朝苗乱相比,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乾嘉苗变是被降苗终止的。
在明朝,明军在生苗区剿苗过程中,生苗没有“不战而降”、“整寨投降”的情况,偶见个别战役中,在战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有临阵投降乞命的。明朝的苗叛,多次都坚持数年甚至十多年,甚至发明了游击战并娴熟地运用。这与乾嘉苗变降苗如云的情况相比,有天壤之别。
在“开辟苗疆”以前的生苗时期,因生苗区没有土地私有,没有奴隶主、地主,没有政府机构,所以,生苗的人生依附关系显得极为特殊。生苗聚族而居,即同一宗支聚而为寨。寨小而散,且易分易迁,寨与寨之间的关系便尤为重要,这样寨与寨之间因地缘结成议榔组织,抢团生存。因此,生苗与宗支的寨形成人身依附关系,与议榔形成人生依附关系。但这种议榔是原始民主平等的,可分可聚的。在没有外部因素强有力干扰的情况下,整个生苗区的社会秩序,依靠各个议榔组织之间力量消涨来平衡的。明朝在生苗区剿苗时,因把生苗视为“化外之人”,不加区别的剿杀,所擒妇幼均“给予军士”,使生苗同仇敌忾,战也是战,不战是死,迫使生苗选择了战。整个生苗区成了战场,生苗与明军展开了山地游击战。直到生苗人尽物尽方止。休生养息几代人,战火又起。所谓“三年一小乱,六十年一大乱”是也。清“开辟苗疆”之后,改变生苗与“化外之人”的政策而视生苗为“编氓”,系取“民苗一体”的汉苗同等对待政策。在乾嘉苗变时,清廷对遇难民人(汉人)的保护和民苗一体的宣传,使生苗看见了投降即可享有与汉人一样的安全,投降还可使苗酋当官等奖偿,于是降苗如潮。清廷强有力的干预,使苗人有了投降的可能和必要。因此,此时生苗的人身依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即从依附于议榔改变为依附于朝廷。
情愿投降的生苗,最终都投降了。“自知罪不赦者”的不愿投降的生苗,后来都去了哪里?据《宣恩县民族志》载:“乾隆、嘉庆年间,清王朝对湘西、黔东北的苗族进行大规模镇压,致使苗民大量逃亡,其中相当一部分迁入宣恩境内”。据伍新福《苗族史研究》载:“贵州紫云、望滇……广西南丹……这两部分苗族都相传是乾嘉起义失败后,由湘西辗转迁去的”。
“不相统属”,在乾嘉苗变后已成事实上的不存在。生苗自己主动选择了投降,即接受了“统属”的事实。而剩下的“不相统属”只是观念上的“不愿承认”的理念,只是一种心理的抗拒。
五、乾嘉苗变的余波
部分研究者认为,乾嘉苗变前后历时十二年。但认真查阅嘉庆二年三月清军主力移至湖北、四川后,生苗区的苗变事件,发现之后十年间的苗区事件与乾嘉苗变有本质的不同。
1、嘉庆三年六月镇筸黑苗抢割民田稻谷事件。
磨岩寨陇满尔、天星寨陇老三等十余苗酋“起意出外抢割民田稻谷”,“纠众数千”,在“高楼背、晒金塘、得胜营一带二十余里”“图割民田禾稻”。
这与传统意义的“寇边”没什么区别,仅是一局部区域的盗抢案件。是役,清兵动用一千五百兵。
2、嘉庆四年九月吴陈受纠约欲图抢夺民屯事件。
“镇筸有营黑民吴陈受为首,吃血纠约火麻范、欧阳坡等七寨苗匪欲图冲卡出外,抢掠泸溪、麻阳民屯粮食、苗兵不能约束”,“十余次扑不动,势渐解散”。是役,清兵动用一千五百兵。这也是一件区域性的盗抢案件。
3、嘉庆五年四月,三厅“夺牛阻耕事件”
乾州麻里湾苗吴老麻、吴老瘦“图占强虎汛附近民田,经苗吴老季理谕不服,纠集多人将该打伤,并枪毙苗兵一名”。
“有苗匪叠次至傅家坝、黄岩江附近一带阻耕夺牛,俱经督率兵勇击退,先后伤毙三十余名,夺回牛只,给还农民”。
这也是数件普通的局部盗抢事件。
4、嘉庆六年二月,铜仁石岘烧抢四十八处民村事件。
铜仁石岘苗寨,乾隆六十年苗变时,未剿而降。因想效仿乾嘉苗变时楚苗多抢多得,事后又分占汉民田地,因而十四寨歃血盟誓,同时邀请湘西苏麻等寨苗人参与。三月初一,一举占领四十八处民村。遇难汉民一万多人,经一万余清兵于同年五月剿灭。参与的三百余名湘西苗民,除剿灭外,余数擒获。
这也只是区域性的局域盗抢事件。
5、嘉庆十年永绥厅石宗四、石贵银“抗缴械,阻丈田”事件。
嘉庆“七年九月,(永绥)厅既移出,群苗争占旧城,弥月枪炮闻黔境。鼎以乡勇数百名深入弹压。忍远近苗大集,鼎急据吉多寨,苗数重环之,铳如雨骤,鼎按兵不动,俟以奇计穿围去,苗疑不敢逼。然自此遂议缴枪械,以绝其牙距”(魏源《圣武记》)同时,傅鼎在生苗区强力推广屯田。永绥八里丁牛寨苗人石宗四,原为吴八月手下大将,“嘉庆二年随众投降,兔死鞍糜”。石宗四系当地“强苗”“富苗”,有田地上千亩。所以,他与石贵银联合于嘉庆十年二月初一起事。当月,石宗四被生擒。
这是一件对清廷缴枪械、屯田政策等的反抗,也是一个区域性的局部行为。
大凡主张乾嘉苗变历时十二年者,多举以上五例以证之。但认真考量之后,以上五例另为乾嘉苗变后连续十年内发生,但与“逐客民复故土”的乾嘉苗变有本质区别:
1、乾嘉苗变反映的是民族矛盾,是生苗与汉族之间的矛盾。而前三例,与传统的寇边无异,图财产而已。第四例,湘西苗人参与铜仁石岘苗人的烧抢行为,原因是石岘苗人承诺分给湘西苗人抢得的钱粮。第五例是对傅鼎屯田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差异不满,而引发的局部骚扰。这些与“逐客民复故土”是不相干的
2、议榔的形式不同:乾嘉苗变的议榔是生苗区全体苗人 必须遵守的,是“大寨并小寨”囊刮了所有苗寨。因此,大寨裹胁小寨,“强苗”、“富苗”裹胁“穷苗”是不可避免的,降苗之祸预先已埋下。而该五例事件,事前都通过议榔,但其成员是局部的,榔众是自愿的,因而没有出现投降现象。
事实证明,乾嘉苗变的议榔—全域性议榔是不合时宜的。在政权的背景下,议榔的榔款,只能处理族内事务(类似于现代的乡规民约),因为,议榔毕竟只是习惯法,而不是法律。
结语。
1、乾嘉苗变,是一场由生苗发动的在生苗区驱赶汉人的战争。最终,主张抵抗的生苗被迫逃亡,剩下的全是降苗。
主动追求去国家化的生苗时代结束了。被动的国家化—后生苗时代拉开序幕。
2、议榔制度,是以原始民主平等为核心的,是以无主土地为条件的。在财产私有的制度下,在国家统治的区域,这种本应消失的习惯法,如果其榔款违反成文法,只能带来灭族的后果。
3、生苗以投降的方式,表达了被动接受国家统治的事实。但其“不相统属”的观念,要与主流民族的文化相融合,仍有极为漫长而又艰辛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