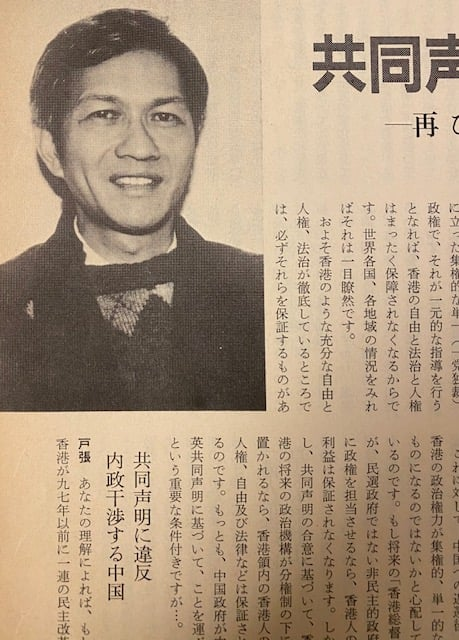图,《中英联合声明》公布后,接受日本杂志的长篇专访。
李怡《失败者回忆录》:「爱国是无赖的最后防线」
(失败者回忆录0209)
徐复观先生在专访中谈到中国文化、国族命运时声音嘶哑、眼含泪光。我在写悼念他的长文写到最后,也忍不住泪流满面。因为我们虽然都在批评中共国,但所有的批评,包括徐先生向廖承志说的四点意见,都是出自对中国的感情,他在讲「党有功有过,国无功无过」那段话之前,还说了这样一段:「共产党最基本的问题是:你要爱国首先要爱我共产党,你不爱我共产党就是反革命,就不算爱国。那我现在问:你做得一塌糊涂,我并不爱你共产党,我只爱国家,这样算不算爱国?」显然,他认为「爱国不爱党才是真正的爱国」。我当时也认同这种看法。
我们对中国的感情有历史根源——中国近代史充满苦难:满清腐败,列强侵凌、日本侵略、多次内战,百姓遭殃。稍有良知的读书人都怀有爱国救亡之心;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入认识者如徐先生,说他在学校每开《论语》课,都怀着感激心情,这种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自然也深化对中国的认同。那时的香港,宗主国英国从不向市民宣传「爱英国」,而香港人若关心政治,也不关心英国或香港本土的政治,而是关心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政治。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在新亚传授儒家文化,其客观效果固然使学生对文革毁灭传统文化反感,也增强了学生从对中国文化的认同,而产生「爱国」不爱党的思想观念。那时候,很少香港华人说自己不是中国人。
文革后,毛泽东那一套「继续革命」「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思想教条,在全国包括中共高层已经没什么人真正相信了。为了巩固政权,从那时起,中共就极少讲马列毛思想,而是大讲特讲爱国主义,用多数人与生俱来、未经思考的民族主义感情去凝聚民气,而真正目的则是利用民族感情去维护政权的合理性。
1981年《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文章,呼吁「发扬爱国传统,立志振兴中华」。这一个指导思想,虽经中共几代领导的转换,也没有改变。什么「共产主义理想」早被中共抛到九霄云外了,只有在领导人作报告时提几句。
然而,在中共具体施政时,并不是以「爱国」作为判定「是敌是友是我」的准则,而仍然一贯地以「爱党」作准则。实际上,爱国是没有准则的,而爱党却有准则,准则就是要跟随此一时彼一时的党的政策或指令。以爱党的准则去衡量爱国,于是长久以来,可以说一贯地,就是如徐先生说的「你不爱党就不算爱国,就是反革命」。
我很早就从自身所受到的对待中认识到这一点,因此,长久以来,对于「爱国」已经被「爱党」骑劫了的政治现实,在言论上不遗余力地批判。批判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是我办政论杂志、写政论文章数十年来针对各个具体事情所作的主要论述。若把所有这些文章汇集起来,可以出好几本书了。
就记忆所及,对于爱国主义,我的论述大概有几个方面。
一是何谓国,二是何谓爱,三是何谓主义。
国家的定义按国际法规定包括三元素:人民、土地、主权。在中国出版的《辞海》中,就根据马列主义的解释,指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一个阶级统治其他阶级的合法暴力机器。不过,出于维护统治者的目的,中共已经不讲这个马列定义了,虽不讲,实际上所贯彻的就是这一个定义。
按国际法规定的三元素,何者为先,决定了国家的性质。由全民定期投票授权领导人的国家,是主权在民的国家,人民掌有领土和主权。一党专政的极权国家,主权、领土、人民都在党的手里。国家机器就是党的权力。
中国先秦时代,虽未有民主观念,但已有「以民为本」思想,即《尚书》所说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社稷可以狭义地解作土地,君可以广义地解作主权。三者以人民最重要。 《孟子》又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个人自身为本、家为本,有家才有国。因此,说「没有国哪有家」,就是专权政治「以党为本」的思想。
何谓「爱」?爱是一种感情。感情是一种难以衡量、计算的东西,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就说明在感情支配下,人不是理性的。捷克作家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一篇文章中说,「人不能没有感情,但当感情本身变成某种价值、衡量是非的标准,或是开释某种行为的借口时,就变得非常危险。最恐怖的罪行往往出于最高贵的爱国情操,而人……在圣洁底爱的名义下杀人放火。」
何谓「主义」?主义代表理念或有完整体系的思想。爱国的完整体系和思想是什么?从来没有人讲清楚,也许最清楚的是18世纪英国作家约翰逊(Samuel Johnson )的定义:「爱国是无赖的最后防线」。
(待续)(106)
(《失败者回忆录》在网络媒体「matters」从头开始连载,网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