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秃笔的老萧发表日期:2024.3.19来源:微信公众号“老萧杂说”
邯郸三名初中生杀人埋尸案,让人沉重到不能呼吸。
孙立平教授今天就此撰文,题为《不想讨论别的,就想问一个问题:那三个少年,何以残暴至此》。
文章讲了四个故事,其中两个,有关人与人;另外两个,有关人与动物。
故事讲完,答案呼之欲出。孙教授终归没有直说,只是抛给读者一连串问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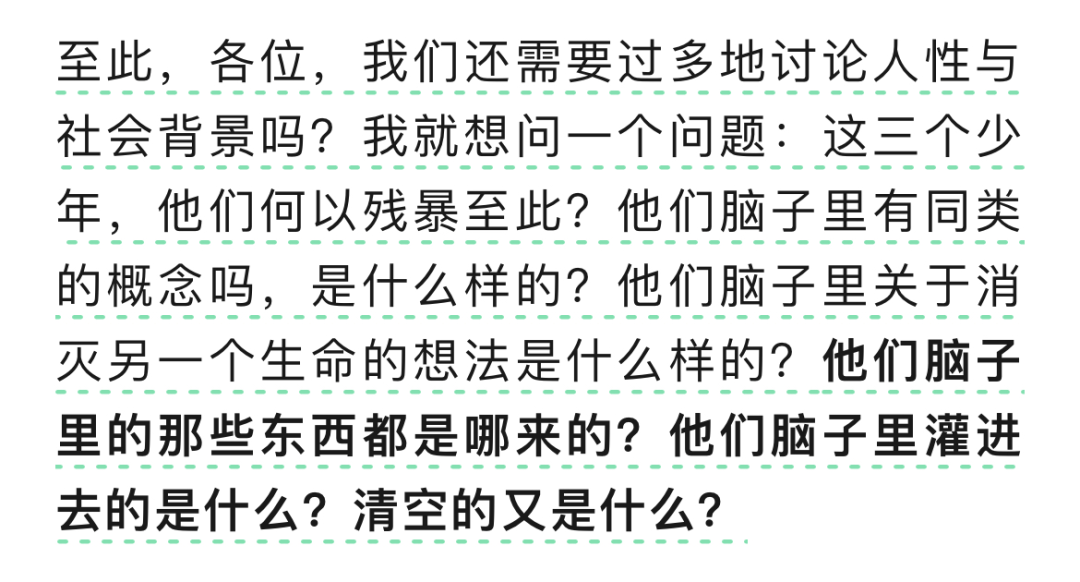
年龄大了,见不得杀戮。对于此案中的血腥惨烈细节,几乎没有勇气细读,只是记住了两个案外的情节。
第一个是,拘押中的三名少年凶手,翘着二郎腿,脸上充满笑意。
第二个是,一人事发后躺在床上打游戏,第二天还能若无其事地去上学。
这种气定神闲,比杀人埋尸本身更令人怵惕。也正是这一点,同样刺中了孙教授。
案发后,校长说学生遇害纯属意外,班主任也很好,遇害者生前在学校没有受到欺凌。
这难免有推卸学校责任之嫌,但我还是选择相信校长。那么问题来了,或许校长也不明白,抑或没来得及思考,自己的学生何至于残暴至斯。
如果有机会,很想抛开事件本身,跟这位校长聊一聊,在其从教生涯中,有没有向学生施加过“仇恨教育”的东西——倘若有,或也会被其认为这没什么不好,属于正确的事情。
暂不论家庭教育,无从知道邯郸这三个少年,在各自成长的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学校教育。
决计相信他们在学校里,虽然未必经历过拿“枪”刺杀安倍、背炸药包之类的游戏——这些在校园里真实发生过,却大抵不是以爱心取代敌意、以悲悯取代强蛮、以宽厚取代偏狭为根本取向的教育。
事实上,每个人都有幽暗、残暴、非人性的一面。生活在高压或无序社会中的人,只要有合适的土壤和机缘,人性里的恶就会发芽生长。
好的教育,弘扬人性善的一面,使人内心变得柔和温淳;坏的教育,诱发人性恶的一面,使人沦为禽兽。
根据孙教授讲述的故事,邯郸三少年的恶,连禽兽都不如的。
从生活经验来说,在许多暴力、戾气事件的背后,都有一种极端主义的思想魔影在推动。
仇恨教育、仇恨思维影响之下的孩子,必然从小对周围世界缺乏安全感,对周围人没有真正的信任,长大后与人共事合作也会磕磕绊绊,往往对强者诺诺唯唯,对弱者施予暴戾。
这些年,校园欺凌现象愈演愈烈,很多行为残忍到令人发指,背后很难说没有仇恨思维所强化的极端倾向在起作用。
其实不止于学校。我们成年人的社会,不也每天都能听到对抗那个、抵制那个、平掉那个的声浪吗?总之都是仇恨的声音,且分贝很高。
教育若不以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为基础,终将造成一种精神品质的畸形发展。
一个正在办理移民的朋友表示,下决心出走的最主要原因,是孩子在学校接受的某些教育,令他不解和惊悚。
孙立平教授忧心忡忡却欲言又止的,不外乎于此吧。
老孙荐读|不想讨论别的,就想问一个问题:那三个少年,何以残暴至此?
作者:孙立平发表日期:2024.3.19来源:微信公众号“老孙荐读”
邯郸3名初中生虐杀同学的事件,震惊全国。对于这件惨案的细节和背后深层原因,人们已经进行了许多讨论。
我一点都不想讨论这些问题,尽管这些讨论自有其意义。我就想问一个问题:三个少年,他们何以残暴至此?何以在以如此残暴手段杀人之后,还能安之若素地照常去上学?
所有的细节与此无关,所有的背景与此无关。我就想问,他们为什么能残暴到如此程度?
促使我提出上面的问题,促使我写这篇文章的,是我想起以前文章中引用过的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都是上海纽约大学哲学助理教授袁源在一次演讲中讲的:
第一个故事:是一战时一位士兵在日记中记录的一件事。他在日记中写道:虽然我已经习惯隔着战壕射击敌人,但今天在休战的间隙,我刚好看到敌人在撒尿,这种人所共通的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好像一下子点醒了我,让我意识到敌人跟我一样。面对一个在撒尿的人,我怎么也无法开枪。
第二个故事:在阿富汗,美军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小分队被困在了一个沟壑里,遭遇从一个土坯房里发出的猛烈的射击。在获取了队长的批准后,下士乔瑟夫·西安诺将火箭炮发射器举到肩头,瞄准土坯房开火,炸掉了大半个土坯房。当尘埃落定后,他们才发现,塔利班把妇女和儿童拉到了土坯房里作为人体挡箭牌。据乔瑟夫的战友回忆,当时乔瑟夫只是一个人靠着墙,默默地无声哭泣。乔瑟夫退伍以后无法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夜里也常常受到噩梦的折磨。退伍的几个星期后,他开车撞上了电桩,死的时候才23岁。
对此,袁源老师说:对很多士兵而言,杀人的恐惧,甚至胜过自己被杀的恐惧。
我不知道各位看了这两个故事后是什么感想。请各位注意,这两个故事都是发生在战场。我们都知道战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那是一个你死我活的场景。但即便是在那样的场景之中,我们却仍然可以看到人性的忽暗忽明的存在。
算了,我现在都不想在人性的层面来谈论这个问题了,我们从动物性的层面来说吧:
2012年的某一天,在重庆市巴南区龙州湾,一只黑棕色的流浪狗被车撞倒在地,已没有任何反应。另一只白色的小狗,正用爪子轻抚着它,并不时地用舌头舔着它流血的伤口。由于当时马路上依然车来车往,有行人担心小白狗也会被车撞伤,准备抱它到路边。白狗朝行人叫了几声,不愿离开。交警赶来,将死去的小黑狗抱到了路边,小白狗也一直跟随着。然后他们在路边找了一块空地,将小黑狗埋了。直到这时,小白狗才默默离去。
再说一件动物与人类之间的事情吧。
在卢旺达,动物学家黑斯受伤,躺在地上动弹不了,在那里一边呻吟一边将目光落在一只母猩猩的身上。黑斯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只黑猩猩走过来,坐在离他很近的地方,将脸几乎贴到黑斯的脸上,一动不动地盯着他的眼睛。突然,她用一只手轻柔地扶过黑斯的头发。这个友好的动作母猩猩重复了三次,每摸一次都停顿一下。黑斯被感动了,因为他知道,大猩猩的性情通常都是很暴烈的。
至此,各位,我们还需要过多地讨论人性与社会背景吗?我就想问一个问题:这三个少年,他们何以残暴至此?他们脑子里有同类的概念吗,是什么样的?他们脑子里关于消灭另一个生命的想法是什么样的?他们脑子里的那些东西都是哪来的?他们脑子里灌进去的是什么?清空的又是什么?


